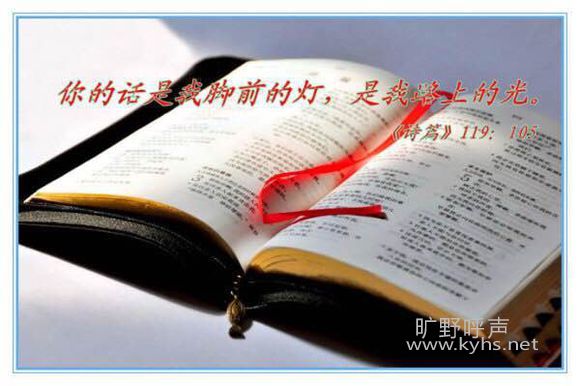我们知道生活并非全是山巅的荣耀时刻——远非如此。有时,谷底幽深,布满痛苦的尖锐岩石和悔恨的荆棘,刺痛我们的灵魂。但关键是:这些不是死胡同,呼召我们更深地倚靠那永不放手的臂膀。
痛苦像波浪一样冲击我们,对吧?可能是失去的痛楚、背叛的刺痛,或者像噩梦般挥之不去的伤害。还记得那个失去一切的约伯吗——家庭、健康、财富——坐在灰烬中,刮着身上的疮?那种痛苦让我们喊出:“我的神,我的神,为何离弃我?”这很真实,很人性,感受它没问题。但我们不困在那里!我们学会视痛苦为炼金之火,烧去杂质,显露更纯净的本质。
查尔斯·司布真,多年与抑郁和身体痛苦搏斗,却说:“我学会亲吻那将我推向磐石的波浪。”波浪虽猛烈,却推我们靠向那不可撼动的根基。司布真知道,痛苦不是无端的残酷;它是慈父手中的工具,塑造我们心向永恒。约翰·派博也说:“当我们在丧失中仍满足于神时,神最得荣耀。”我们最深的伤痛成了神圣荣耀最闪耀的舞台。不是否认伤害,而是将忧虑交托给那关怀我们的祂。
还有奥古斯丁,他的《忏悔录》描述,他曾追逐空虚的享乐,历经动荡,最终找到真安息。他写道:“在我最深的伤口里,我看见你的荣耀,它令我目眩。”痛苦成了通往荣耀的窗口,就像那珍珠的比喻;我们得舍弃一切,承受损失,才能抓住真正宝贵的。在我们破碎时,痛苦剥去伪装,创造主便开始重建。
但痛苦不只是外在的;它常与悔恨相连,那种“悔不当初”的啮咬,萦绕在安静时刻。悔恨像过去错误的阴影——收不回的话、走偏的抉择、错失的机会。就像浪子盯着猪食,意识到自己堕落多深。恩典唤醒了我们的良心,然而,沉溺于悔恨不是出路;它是个陷阱,让心更硬。
清教徒约翰·班扬,那个在牢房写作的补锅匠,警告说:“若你犯了罪,不要不悔改就躺下;因为不悔改会让心越来越硬。”他说的太对了——没有转向的悔恨只是伪装的自怜。真正改变来自转向怜悯,坦白并接受宽恕,像呼吸空气般自由。C.S.刘易斯说:“这个世界对你如此美好,以至于你舍不得带着悔恨离开吗?前方有比我们留下的一切更好的东西。”刘易斯,失去妻子后与怀疑角力,催促我们向前看。悔恨在注视奖赏、生命之冠时失去控制。
约翰·加尔文教导我们悔改不仅是罪的悲伤,而是一生的转向,喜乐地回到父家。就像那个用泪洗脚的女人——她的悔恨化为丰盛的爱。派博一针见血:“为自己的错感到难过感觉很对——很属灵——但几乎从不让你做得更好。”多刺痛啊!悔恨可能伪装成虔诚,但真正转变发生在救赎的光中,旧事已过。
路德坦诚:“我的悔改本身也需要悔改。”提醒我们都在进程中,依赖不配得的恩惠。司布真补充:“世人眼中的小罪,对真信徒是大罪。”所以,别轻忽悔恨;我们要直面它,但通过十架视角,那里一切债务已清。
在我们的情感生活中,痛苦与悔恨不是独自击败的敌人——它们是来就安慰者的信号。如同陶匠与泥土,祂通过试炼塑造我们,将灰烬变为美丽。刘易斯曾说:“神在我们的快乐中低语,在我们的良心中说话,但在我们的痛苦中喊叫:那是祂唤醒聾病世界的扩音器。”对悔恨,它是鞭策我们跑向敞开怀抱的杖,如同父亲拥抱归来的浪子。
我经历过,凝视自己的失败,感受失去的刺痛。但每次,轻吟“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”。我们变得更坚强,预备用我们所得的安慰去安慰别人。所以,别让这些情绪锁住你;让它们推你进入更深的信靠。大牧人领我们穿过幽谷,苏醒我们的灵魂。坚持下去——黎明将至,带来无以言表的喜乐。
赞助商链接
- 本作者更多文章
- 穿越心灵风暴:视痛苦为炼金之火2025-08-29
- 操练感恩,从哪里开始呢?2025-08-15
- 修剪的痛,是为了让生命更丰盛2025-07-24
- 信与不信:生命轨迹的分野2025-07-03
- 怜悯就像播种,你撒下的每一粒种2025-06-27
- 筑起生命的篱笆,这界限,不是限2025-06-20
- 请不要将“顺服”用来“信仰PUA”2025-06-18
- 财富转换的密码2025-06-17
- 戴德生的见证2025-06-06
- 赞助商链接
- 相关文章
- 热门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