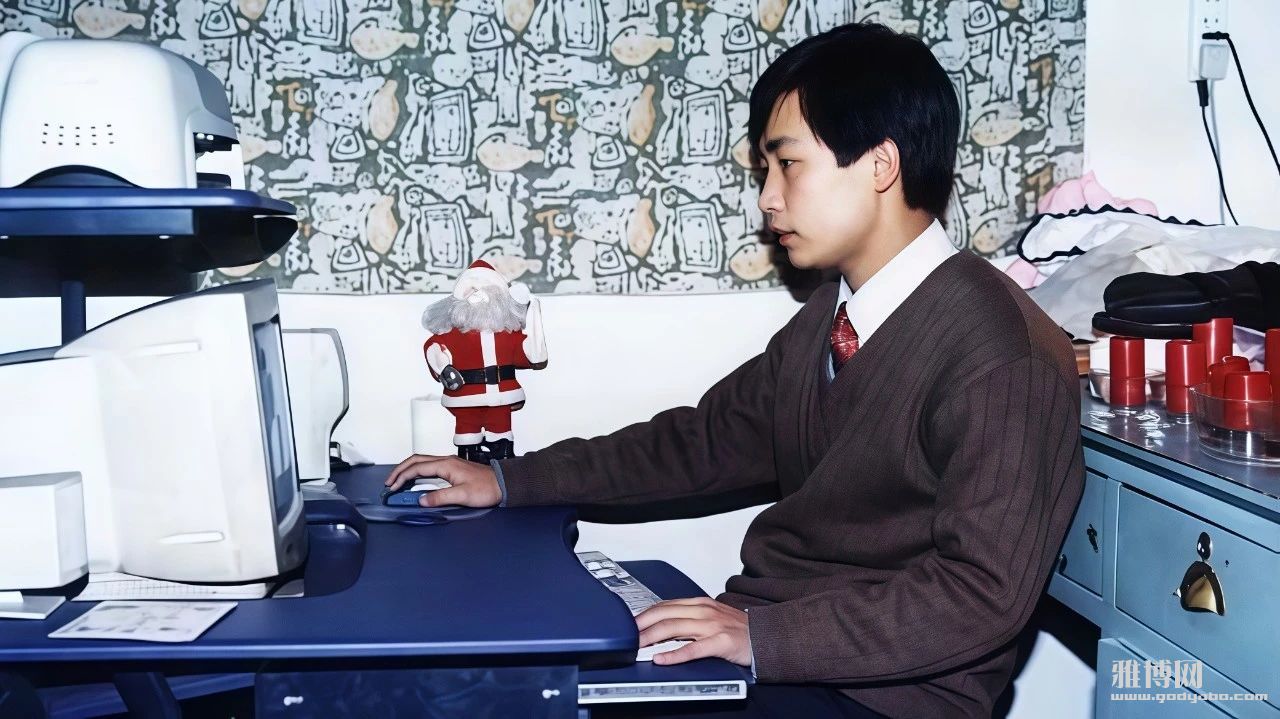
经文:王上19:9-18
何烈山上,以利亚听见来自天上的声音:“以利亚啊,你在这里作什么?”听过这话,先知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,毁坏了你的坛,用刀杀了你的先知,只剩下我一个人,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”之后,以利亚听到一段让他倍感羞愧又倍受鼓舞的话:“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,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,未曾与巴力亲嘴的。”
以利亚时代的以色列人已有数百万之多,那“七千人”显然只是少数,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不是先知,也不是祭司,他们没有响亮的名声,没有显赫的成就,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天父的虔诚和敬畏。以利亚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,身在何处,但他从他们身上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舞!
无论教会多么衰落,牧者多么昏庸,信徒多么冷淡,每一个时代,教会里都会有坚守纯正信仰、不向世俗妥协的“七千人”,这个群体的存在,是忠心侍奉者最好的安慰,最大的鼓舞,最强的动力!
傅士德(Richard J. Foster)曾这样说:“我们这个时代的祸因是浅薄。事事寻求立时的满足乃是一种基本的灵性病症。今天最迫切的需要,不是聪明能干的人,或大有恩赐的人,而是有生命深度的人。”繁忙、浮躁的现代人严重抗拒深度阅读,多数人只能接受140字的微博和30秒的抖音。在这样的时代写文章,像极了纳鞋底、磨菜刀和编箩筐,可能有人赞叹他们的“手艺”,但极少有人需要他们的“产品”。即使如此,依然有一批忠心的牧者坚持写作,因为他们坚信,无论社会多么纷乱,无论人心多么浮躁,这个世界总会有“未曾向巴力屈膝”的“七千人”,这些人需要优质文字的滋养!
我的社会学历只是初中,本来不具备写作的条件,但我刚读神学就开始学着写作,因为我那时就相信文字的力量。尽管在专业人士看来,我的作品充其量不过是信手涂鸦,但我早就把写作当成了上主给予我的恩赐。我的这样恩赐,不及前辈的“五千两”,不及同辈的“两千两”,但我不垂涎别人的“多”,不抱怨自己的“少”,只会尽我所能,让这“一千两”发挥其最大的功用。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聪明的人,但我敢说自己是一个勤奋的人。8小时之内,我有很多工作要做,所以我的写作时间都在8小时之外。早晨5至8时,晚上 9至0时,每天写作6小时,20多年,几乎天天如此!
有人说,信息在互联网上传播,经历了三个时代:文字时代、图片时代、视频时代。身在视频时代,却固执地坚持文字创作,注定不会受人待见,但遭人嫌弃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想象。我在抖音里随便胡说八道一通,任意发一个视频,几千、上万点击量,但在公众号里发一篇绞尽脑汁的原创文章,却很少有人阅读。我常如此自嘲:“一通操作猛如虎,阅读不足250。”然而,只要有人阅读,我就没有理由不写。近些年去外地出差、讲道,常有人对我说:“李牧师,我是你的‘粉丝’,天天都去自留地!”起初,我以为人家这样说话,只是比较礼貌而已,后来发现,有人居然能说出文章的题目,记得文章的观点,真的被大家的用心阅读感动了,他们给予我的鼓舞,像极了那“七千人”给予以利亚的鼓舞。故此,当我对阅读量感到失望的时候,我常如此自勉:毕竟还有“七千人”!
写作真的很苦,很累,我常如此调侃:构思时搜肠刮肚,脑袋疼;写作时正襟危坐,颈椎疼;写好后无人问津,胸口疼。即使如此,真的让我放弃写作,我既不甘心,也不忍心。不甘心,是因为我不能轻看“一千两”的价值;不忍心,是因为我不能漠视“七千人”的需求!今天起,我的座右铭就是:用好“一千两”,服务“七千人”!可是,怎样才能把我的“一千两”,送到“七千人”的手中呢?这是一个问题!我想起了司布真(Charles Haddon Spurgeon)的一段话:“我不断地祈求上主开一条敞开的路,使好的作品能到需要者的手中。”我也要如此祈祷,你可以与我一同恒切祈祷吗?
2025年8月26日清晨于养心斋
赞助商链接
- 本作者更多文章
- 用好“一千两”,服务“七千人”2025-08-31
- 此生难忘的三个“我愿意”2025-08-17
- 禁戒肉体的私欲——从一位知名僧2025-08-03
- “以直报怨”与“爱人如己”2024-07-07
- 我相信文字的力量2024-06-30
- 父亲,我的良师益友2024-06-16
-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2024-05-26
- 不可吃血2016-04-19
- 赞助商链接
- 相关文章
- 热门文章
 天地同歌·耶希亚巡回音乐布道会
天地同歌·耶希亚巡回音乐布道会
作者:罗博学 2013-05 于软弱中见刚强——悼念杨贞(爱道)姊妹
于软弱中见刚强——悼念杨贞(爱道)姊妹
作者:黄爱明 2009-02 我向耶和华歌唱
我向耶和华歌唱
作者:张路得 2015-07 不可论断神的仆人
不可论断神的仆人
作者:陈克奇 2019-08 《耶米玛讲道讲章选集》出版了
《耶米玛讲道讲章选集》出版了
作者:耶米玛 2014-12 没手、没脚、没烦恼!
没手、没脚、没烦恼!
作者:Nick 2007-10 我的侍奉之路
我的侍奉之路
作者:舒亚 2014-06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