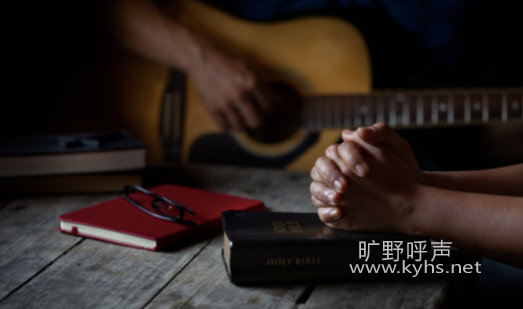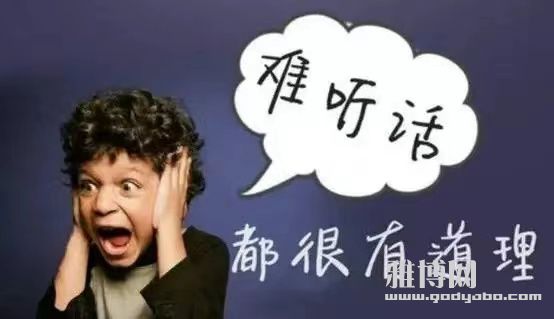自从回到阿爸的家里,我突然发现,我有了许许多多的亲人,伯笠四哥就是其中的一位。不久前去开华人牧者的特会,我又一次见到了他。他告诉我,他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随同三哥一起在龙口定居了。那时我就在想,四哥不能回来,我就替他去看望他的亲人们吧。
与四哥相识,源于我对异端“马可楼运动”的口诛笔伐。战火正激,四哥来看我的博客,留言说:“好厉害的一支笔!”他的到来,得益于远在华盛顿的另一位亲人国俊的引见,很快,我就在当年的华人牧者特会上见到了四哥。
再一次相聚,我更认识了老母亲、三哥三嫂、妹妹妹夫,这是一个大家庭,他们与四哥的相见,只能选择香港这个中界地。那一年,老母亲已经八十四岁了,是个端庄漂亮又喜乐的老太太。她还登台唱了一首赞美诗,从她清亮悠扬的嗓音里,我知道了,为什么四哥会有那样一条好嗓子,这是来自母亲的真传。
定下行程的头一天,彤云密布,浓雾弥漫,一副要下雪的样子。我就在心里默默祈祷,让这雾散去,把这云移走,不要成为我们探亲的阻碍。我深知道,阿爸垂听了我的祈祷,早晨八点出发,十一点多就到了龙口的海边,与赶到那里的希菊夫妇和王伟弟兄汇合,在三哥的引领下,进了家门。
三嫂和老母亲迎了出来。较三年前,老母亲并没有大的改变,满脸的慈祥与喜乐;三嫂还是那样率直热情,丝毫没有陌生的感觉。老父亲也从卧房中迎出来,坐在客厅里和我们交谈,三哥三嫂忙着端茶倒水削水果拿瓜子,招待我们。孩子们立刻被窗外近在咫尺的大海吸引住了,她们涌到阳台上,一边观看,一边拍照,家里立刻热闹起来。
我和希菊还有孩子们,陪在老母亲旁边,执手唠嗑儿,弟兄们就围在老父亲身边,说着家常。四哥一家都是东北人,乡音无改,十分亲切。我告诉老母亲和三哥三嫂,去年2月,我被按立为牧师,三嫂听了特别开心,说“咱们已经是牧师了哇?”我告诉他们,在按立牧师之前,我曾征求四哥的意见,得到了他诚挚的鼓励和祝福,四哥在邮件中,祝我“居上不居下,居首不居尾”,勉励我甘心摆上,作合用的器皿。是这样的鼓励,坚定了我的心志,让我勇敢地回应阿爸的呼召。
我还告诉他们,不久前见到的四哥,仍然充满激情。作为大会的执行主席,他是最为繁忙的一位,但是他仍然坚持每天带领大家晨祷,也每天接待各地的亲人到深夜。当然,这后一句,只是我的听闻,依照我的意思,我是不会去打扰四哥的,哪怕心里存着讨教的心,也不愿加重四哥的负担。我和希菊是在一个早餐会上,偶遇了四哥,四哥立刻放下围在他周边的朋友们,说“我的老朋友来了,对不起呀”,抽身出来和我们一一交谈。我没有说到,四哥因为到处奔走的缘故变得略带倦容,有些苍老了,有些消瘦了,我只能说,他很好,一点都没有变,还是那么忙,还是那么受人尊敬和欢迎,还是那么惦念家、惦念亲人。
想到四哥竟然不能回到家里,来看望亲人们,我鼻子发酸,禁不住落下泪来,三嫂也红了眼眶。我一一打量着亲人们,我要把他们深深印在脑海里,要告诉四哥,他们很好,很平安,很喜乐。我祈祷并且深信,在不久的将来,四哥一定会远涉重洋健步归来,我深信并且祈祷,已经年过九秩的老父亲和八十七岁的老母亲一定能健康长寿,等待他们的儿子到来。
我们又进了三哥三嫂的卧室,这里有一扇弧形落地大窗,将海面尽收眼底。三嫂说,在其他的季节里,这里不时有帆船划过,有时还会在海滩上看到海豹们嘻闹的身影。这是一处内陆海湾,我在青岛海边听惯的风的嘶吼,在这里完全没有,宁静得十分美好。
时光在诉说不完的家常话里飞逝,一个多小时过去了,我们起身告辞,三哥三嫂说什么也不允我们这样离去,一定要陪我们午餐。我拥抱着老母亲,又一次禁不住流下惜别的泪水。老母亲站在我们中间,唱起了祝福的赞美诗,唱得我们的心更加柔软。我们手牵着手围成一圈向阿爸祈祷,祝福这一蒙了大福的家庭,祝福每一位亲人,祝福老父亲老母亲健康长寿,也祝福远在大洋彼岸的四哥服侍更加得力,祝福他能够早日踏入家门。
三哥三嫂点了许多牛羊肉、海鲜、青菜,弟兄一桌、姐妹一桌,欢声笑语不断。我想起有一次在博客上晒与女儿一起在家里吃火锅的照片,四哥看见了,留言说:“我也想吃!”想到他几次足临国门却不得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,我的心里就忍不住发酸。这一回,我还给亲人们带了我新出版的散文集、新歌的CD,还当场献唱了一首高原风格的“神是我的产业”,三嫂一直夸赞说“好听”,要我把我的新歌曲谱全部寄给她,因她在诗班里还是主力。
挥手告别三哥三嫂,已是午后两点多了。回程的路上,我们一直在交谈信仰的话题,在唱赞美的诗歌。想念着刚刚分别的亲人们,想念着在天上的阿爸,几度欢喜,几度流泪。彤云早已散去,浓雾也存留不久,我深信,我们一直的思念和祈祷都不会落空。
亲人们,我们还会来看望你们的。
。
赞助商链接
- 本作者更多文章
- 赞助商链接
- 相关文章
- 无相关信息
- 热门文章
 圣经对妻子的六个要求
圣经对妻子的六个要求
作者:张远来 2018-05 贤惠妻子,丈夫的冠冕
贤惠妻子,丈夫的冠冕
作者:佳音 2018-04 基督徒可以离婚再婚吗?
基督徒可以离婚再婚吗?
作者:张远来 2016-09 好妻子是怎样炼成的
好妻子是怎样炼成的
作者:未知 2011-05 今年高考,基督徒父母当如何为孩子祷告?
今年高考,基督徒父母当如何为孩子祷告?
作者:耶稣爱你99 2017-06 不可离婚的原理
不可离婚的原理
作者:海夫 2012-12 青年节,为青少年献上祷告
青年节,为青少年献上祷告
作者:耶米玛 2016-0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