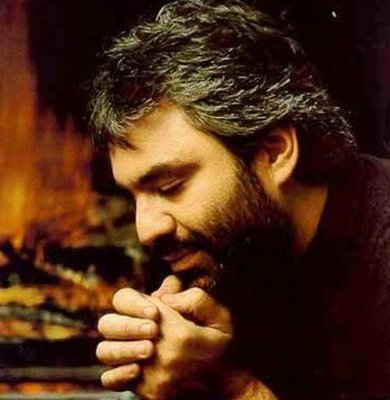释经学(Hermeneutics)源于希腊文的一个字,意思是「解释」。传统上它是指「解释作者意思的原则或方法之科学」;不过,有人向这种说法挑战,而今天在许多圈子内,这个词已经只指说明经文目前的意思,与它原初的意义无关。这是本书两个附篇所探讨的题目,在那里我提出的看法为:对原初意义的关注仍旧是释经学的重点,这是合理的,甚至是必要的;释经学探讨经文过去的意义,也探讨它今天的含义。我反对今天有些人用「解经法」(exegesis)称对经文意义的研究,而用「释经学」称它对现今的意义。其实,释经学是含括一切的名词,而解经与「处境化」(contextualization,指将经文对今日的含义作跨越文化的沟通),乃是这个大任务中的两方面。 若要正确明了释经的任务,必须具备三个观点。第一,释经学是一门科学,因为它按照逻辑和分类法,提供了解释的定律。在本书第一部中,我将根据相关学科--如语言学、文学批判等--所提供的大量资料,重新设定解释的「定律」。第二,释经学是一种艺术,因为它的技巧要求具备想像力,并能够将「定律」用在特定的经文或书卷中。这绝不可能只靠在课室中学习,而要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操练,才能有所成就。我将从圣经本身举出许多例子,展示释经的「艺术」。第三点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:用释经学来解释圣经,是一件属灵的事,必须倚靠圣灵的带领。现代学者常太忽略神的层面,只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圣经,几乎将有关神的一面当作文体(genre)看待。但是人的努力并不能使神的话语真正成为上头来的信息。巴特(KarlBarth)教导说,圣经的作者只是工具而已,这个观点固然不正确,但是他强调,圣经向人类说话,是透过神所掌控的「亮光」,这个见解却一点也不错。在研读圣经的时候,我们必须倚赖神,不能单单倚赖从人得到的释经原则。有关「光照」的教义,以下有一章将深入讨论。 释经的工程也有三个层次,可以从代名词的角度来予以界定。首先是第三人称的角度,所提的问题为「它的意思为何?」(解经);接下来是第一人称的角度,即是问「它对我有何意义?」(灵修);最后则是第二人称的角度,尝试「与你分享它对我的意义」(讲道)。 这些层次并非互相排斥,而是彼此倚赖。福音派的释经学过去只以第一个层面为主,而将其他两个层面留给讲道学。存在派的释经学一直以第二或第三个层面为中心,有人甚至主张,第一个层面已经与今天无关。事实上,就整全的方法论而言,这三个层面缺一不可。若忽略第一个层面,就是进入无法控制的主观世界,任何人的观点都没有高下之分(附篇(一)中的「多重意义」)。忽略第二个层面,就等于挪去圣经的根基,不理会个人与神的相遇--这种相遇会要求人改变生命。忽略第三个层面,就是删除圣经的命令,即神的启示乃是好消息,要与人分享,不可以只给自己享用。诠释者必须按这个顺序,才能将圣经处理得当:以圣经原初的意义为基础,再在其上建造对自己的意义,以及对我们所事奉之人的意义。举例来说,如果从第一步跳到第三步,就成了假冒为善,因为我要求会众或听众去做的事,自己却不实践。 本书的前提为:圣经的诠释--从经文到处境、从原初的意义到处境化的应用(或对今日教会的重要性)--乃是「螺旋式」(Spiral)的。自从「新释经学」以来,学者喜爱用「释经学循环」(hermeneutical circle)一词,描述我们对经文的解释导致它解释我们。然而,这种封闭式的循环有危险性,因为其心态为「语言事件」是平等的;这样一来,经文的首要性便丧失了(参Packer 1983:325-27)。「螺旋」的比喻则较佳,因为它不是封闭的循环,而是一端敞开的运转--从经文的水平走向读者的水平。我不是绕着封闭的圈子来回转,找不到真正的意义为何,而是沿着螺旋走,可以愈来愈靠近经文原初的意义;也就是说,我必须作精辟的假设,并且不断让经文向可能的解释发出挑战,加以修正,再引导我来说明它对现今状况的重要性。圣经作者原初的意思是很重要的起点,但本身却不是终点。释经学的使命要从解经开始,可是要到将经文的意义处境化,应用于今日的情形,才算完成。释经的两方面,就是赫尔胥(Hirsch)所谓的「意义」与「重要性」,或对原初作者和其读者[所谓「听众批判」(audience criticism)]的意义为何,以及对现代读者有何重要性(1967:103-26)。 释经学很重要,因为它使人从经文走到应用,让神的灵所默示的话语,以新鲜而满有活力的方式向今天的人说话,像当年一样有力。此外,传道人或教师必须宣扬神的话,而不是讲他们自己主观的宗教看法。惟有经过仔细界定的释经学,才能够使人与经文牢牢结合在一起。我们这一代福音派最基本的错误,是「引用经文作证明」,就是以一段经文来「证明」某种教导或作法,却没有考虑到原初神默示它的意义。许多背诵圣经的节目,本身固然很有价值,但等于鼓励人忽略一段经文的上下文,只将其表面意思应用到人的需要中。倘若要将原初意义和现代应用联系起来,需要花许多工夫。 在本书中,我采用「意义-重要性」的模式。这个观念是依据赫尔胥的区分,他认为,作者在一段经文中原初的意思,是不可改变的核心,而该段经文对个别读者的重要性或含义,却有多种形式;原初意义之应用,可以视不同的情境而有变化(1976:1-13)。今天对这个问题的辩论很多,不少人提出挑战。布鲁格曼(Brueggemann)观察到,「『它的意思为何』与『它现今有何意义』的区别,……逐渐被弃置、忽略,或否定。,因为诠释者的先入为主,或「释经的自觉性」(selfawareness),使回到原初意义变成一件很难的事(有人则认为不必再在乎)(1984:l)。然而,我仍然相信,这是最能阐明释经学任务的模式,在附篇(一)与(二)的论点,以及本书的整个进展中,我都将陈明个中道理。 圣经并不是透过「天使的言语」启示的。它虽然是神的默示,却是用人的语言写成,也置身于人的文化中。因着语言的特质,圣经恒常的真理乃是包含在比喻式的话语中;换言之,圣经绝对的真理,是包藏在古代希伯来和希腊的语言和文化之中,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文化,才能正确地解释经文。圣经不会自动跨越文化隔阂,来陈述其意。学者对同一段经文的解释差异甚大的事实,也让我们明白,在读经时,神不会奇迹式地启示经文的含义。尽管福音的真理很简单,但要揭示某段经文原初的意义,却是一件复杂的事,需要下很多工夫。要完成这项艰钜的任务,我们只能尽力研究释经学,并且持之以恒地应用它。在开始这项任务之前,还需要注意几件事。 释经学与经文原意 现代的批判学者愈来愈认为,要发现一段经文原初的意义是不可能的。问题为:作者在写作的时候虽有明确的用意,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道,因为他们不能现身,来澄清或说明他们所写的内容。现代的读者无法从古代的观点来读经文,而必然会不断将现代的观点读进经文中。所以,批判学者主张,客观的解释是不可能的,作者原初的用意,我们已经完全失落了。既然因着团体的不同,「意义」也随之不同,实际上任何经文都可能有多重意义;只要该意义能对特定的阅读观点或团体有作用,便有其价值。 这些问题实际存在,而且十分复杂。由于其中牵涉到艰深的哲学问题,我在此不详谈,留到附篇才深入讨论。然而,从另一个角度而言,本书的每一章,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,因为解释的过程能构成一个基础,来发掘圣经经文原初的意义。附篇探讨的是理论方面的答案,而整本书的努力,则是要提供解决这难题的实际方案。 圣经的默示与权威 圣经自然流露出权威。旧约不断用「耶和华如此说」,而新约中,神所赋予使徒的权柄亦无处不见(参Grudem 1983:19-59)。至于权威的尺度,学界则辩论不休。我支持一种审慎的无误论( P. Feinbers 1979),而不赞成阿克提美亚(Achtemeier 1980)的动态模式;他主张,不单原初的事件是受圣灵默示,连后来的团体所添加的意义,和正典的最终决定,都是受圣灵默示;他又认为,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,也有圣灵的默示。以下的图对释经学很重要,因为它显示出,我们离开神话语原初的意义愈远,与其权威的分隔也就越大。 如图0.l所示,从经文到阅读到应用,权威的程度愈降愈低;因此,我们必须竭力往上,在作应用的时候,尽量接近解释,这样才会连于经文/作者的原初意义/用意。在讲道以及基督徒的生活中,权威的真正途径,是运用释经学将我们的应用连于经文的要义。阿克提美亚说,教会的历史传统与现代的解释都有圣灵的默示,这个看法对经文的首要性不够重视,其实神的话只含括在经文之中。 第一层次 ↓ 经文 ↑ 内在的权威 第二层次 ↓ 解释 ↑ 衍生的权威 第三层次 ↓ 本色化 ↑ 应用的权威 意义与文体相关 在附篇(二)及以下特殊释经学的部分,我将说明:一段经文所属的文体,或文学的类型,成为它「语言游戏的规则」(维根斯坦(Wittgenstein)提出);换言之,就是成为了解它的释经原则。诚然,我们解释小说的方式,与诠释诗的方法相当不同。我们看圣经智慧文学的角度,与看预言也极不一样。但是,有些地方仍会引起辩论,因为显然会有重叠。例如,先知书内有很大部分是诗体,还有一部分为启示文学。启示文学中有书信的内容(启二—三),而福音书中有启示性题材(例如:橄榄山的讲论,可十三,和比喻),书信中也有(帖后二)。为这缘故,有人怀疑文体在解释方法上的价值,认为文体既然会混合,便无法清楚辨认,因此不能作为释经的工具。然而,我们能够在某种文体中辨识出启示文学或诗体部分,正显示出这种方法的功效(更详尽的论点,参Osborne 1984)。 作者用意(赫尔胥称它为「内在的风格」)能否发掘出来,这场辩论中,文体的存在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每位作者都是用某种文体来呈现信息,让读者可循一定的规则来解开作品,得到信息。这些暗示能引导读者(或听者),提供解释的线索。马可记载耶稣讲撒种者的比喻时(可四1-20),特意将它放在一种情境和一种媒介中,以便向读者作最有效的沟通。我们要了解其意义,就要明白比喻的功能(参本书第十一章),并注意在马可安排的情境中,这些象征的功能为何。 圣经的单纯性与易明性 自从前一辈的人提出「信仰的准则」(regula fidei)之后,教会一直在为「圣经的简明度」挣扎;亦即,它是否能够被人清楚了解。常有人指责圣经学者,说他们使圣经与一般人愈离愈远,这不是没有理由的。学术界将圣经肢解,又提出各式各样的理论来解释,平信徒只能徒呼:「好吧!可是圣经对我有什么意义?我能读得懂吗?」当然,初入大学或神学院的新生,发现一段圣经可以有那么多种不同的解释,一定会大吃一惊。一旦知道圣经每一句话都有许多可能的解释,他们就不再认定圣经是容易明白的;这一点实在无可厚非。然而,这是将释经学原则与福音信息混为一谈的缘故。其实,复杂的是如何搭造文化的桥,将原初的情境与现今的状况连接起来,而不是意义问题。 路德[在《意志的捆绑》(The Bondage of thc Will)一书中]宣称,圣经在两方面非常容易明了:外在,他称之为文法层面,即可以将文法的定律(释经原则)用在经文上;内在,他称之为属灵层面,即圣灵会在读者解释时赐下亮光。谈到容易明了,路德的意思显然是指最后的结果(福音信息),而不是整个过程(发掘个别经文的含义)。不过,上个世纪有人将苏格兰式常识主义应用到圣经上,因而许多人假定,每个人都可以自行了解圣经;也就是说,经文的本身已经足以将其意义充分表达出来。所以,大家不再重视用释经学原则来搭文化之桥,而个人化的解释比比皆是。当时似乎没有人注意,这样会造成多重意义的问题。简明的原则也扩及释经的过程,导致一般人解经的错误,以及今日相当困难的局面。其实释经学乃是一门学问,要经过复杂的解释过程,才能揭开圣经原初易明的意义。 然而,这便让人感到困惑,以致一般人会问,是否只有学术界的精英才有资格明了圣经。我认为并非如此。首先,明了可以分好些程度:灵修式、基础的读经、讲道式、作业或论文式。每一种程度都有其价值和一定的过程。其次,凡愿意按程度来学习释经学原则的人,都可以学到。这些原则并不只保留给「精英」,凡是有兴趣、有心力的人,都可以学会。基本的释经学可以在地方教会中教导。在本书中,我希望能顾及不同的程度。 圣经的合一性与差异性 福音派(强调合一)与非福音派(强调差异)对圣经的误会,都在于不能掌握这两种层面的平衡,其实它们是互相倚赖的。差异性是因圣经用语具类比的性质而来。圣经很少有几卷书是向同一个情境说话,因此,在用字和重点方面,差别很大。再者,默示的教义要求我们注意这些圣书背后作者的个性。每一位作者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,所强调的要点,和所用的比拟法也各有千秋。例如,约翰使用「新生命」的用词来表达重生的观念,而保罗则用收养的意象。保罗注重惟靠信心才能重生,但雅各强调惟有行为能表现出真实的信心。这些并非互相冲突,只是每位作者在重点上的差异而已。 问题在于,这些差异是否无法协调,还是以色列与初期教会在各种传统之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之下,有深层的合一。邓恩(J.D.G.Dunn)所著《新约的合一性与差异性》(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New Testament)一书中指出,初期教会有很大的差异性,而贯穿全体惟一的一条线,乃是历史的耶稣与高升之主的连续性。这个合一始于基督论[参邓恩后来所著《基督论的形成》(The Making of Christology)],延伸至圣经论(连于初期教会的信条和耶稣言论集),甚至延及教会论(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强调的论点)。 可是我们不能太过强调圣经的合一性,以致抹杀了约翰或保罗个别的重点。这样作便会产生错误的平行,以致依据某一位作者(如:约翰)来解释另一位作者(如:保罗)的话,这样的诠释肯定有错。不过,在不同的表达背后,却有至为关键的合一性。差异性的概念是 圣经神学的主干,而我认为,惟有圣经神学能将解经与系统神学(以合一性为中心)连系起来。例如,在发展完备的关于坚忍的教义时,我们首先必须让约翰福音与希伯来书充分表达各自的看法,然后才将两者放在一起来看。而合一性的概念则为系统神学的基础。当然,有限的人永远无法作出圣经真理最完整的「系统」;可是,若说我们无法将圣经真理「系统化」,却是不正确的。要诀是让系统出自经文本身,透过圣经神学浮现出来,再按要义分类,扼要说明圣经各种不同表达法背后的合一性。 圣经的类比 路德提出「信仰的类比」(analogia fidei)来抗衡罗马天主教所提的「信仰的准则」(regula fidei)。路德反对以教会传统为中心,而相信惟独圣经可以判断教义。根据圣经的合一性与易明性,他建议,基本的教义应当与整本圣经的教导吻合,而不能相抵触。可是,路德多少仍以整个系统为重。所以,我要提出另一个看法,即「圣经的类比」(analogia scriptura)。德利(M.Terry)的名言仍然成立。「单凭一卷书的某个声明,或某段难明的经文,不可以推翻靠许多经文建立起来的教义」(1890:579)。我要再加强说,教义不可以只建立在一段经文之上,必须要综合圣经对该题目所有的内容。如果没有可助澄清的经文(如:林前十五29所提为死人受洗,或路十六22-26有关阴间的划分),我们就要小心,勿作出专断的声明。 此外,所有的教义(如:基督的主权,或永生的把握)必须建立在一切相关经文之上,不可只建立在几节证明经文,或「偏好」的经文之上。因为这样会造成「正典中的正典」,也就是倚重主观所偏好的某些经文,超过其他经文(因为它们可以配合某个系统);这种作法乃是将系统强加于圣经之上,而不是从圣经中得到系统。这样很危险,因为它假定:我们的先入为主比经文更重要;它也会错解圣经。圣经的话很少会包含整个教义的理论。圣经作者的话,常是针对特定的教会情况,将某项范围很广的教义,应用在一个特殊的问题上,而强调那个教义适用于当时状况的某一方面。例如,保罗的书信都是因事而写,针对当地教会的问题与困难,而不是要将教义作综合说明的神学作品。这不是说,这些作品不具神学性;而是说,各卷书信乃是将一项范围较广的神学(这是我们从「圣经神学」方式所得着的;参本书第十三章),应用到当时的状况。所以,若要建立一项教义,就必须将圣经对这个问题所有的言论都放在一起,找出怎样才是最好的摘要说明。这方式就是我所谓「圣经的类比」。 启示的渐进性 神向他子民的启示有阶段性,这已久为人知。与圣经的类比相关的一个概念,就是:在圣经写作时期,启示不断有新的开展。我们追溯圣经对某些题目的教导,例如多妻制或奴隶制,有一点很要紧的,就是认出这些教义在圣经中的历史发展。然而,后面的经文并不是取代前面的,而是澄清前面的经文,并显示出,在神子民的了解过程中,它们只是一个阶段而已。例如,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5-9节和歌罗西书三章22节对主仆伦理的说明,不能用来「证明」奴隶制的正确。相反的,加拉太书三章28节或腓利门书16节所讲到的平等,以及希伯来人对奴隶制的严格管制(根据出二十一2或利二十五47-55,希伯来人可以在契约之下成为奴隶,可是在安息年或禧年必须得释放),至终瓦解了这个制度。 解经讲道 我要强调,释经学的终极目的不在建立系统神学,而在讲道。圣经的实际目的不是解释,而是宣告;不是叙述,而是宣扬。神的话要向每一代人说,而释经学的任务可以浓缩为:建立意义和重要性的关系。重解一段经文原初的意义还不够,我们必须阐明它对今天的重要性。 李斐德(Walter Liefeld 1984:6-7)说,解经式的信息必须有释经学的正直(忠实地复制经文原意)、前后一致(整体感)、动力与方向(注意到一段经文的目的或目标),和应用(注意到经文与当代人的关系)。若缺乏任何一项,就不算真正的解经讲道。有人误以为,只要解释该段圣经的意思,就算解经。这类讲道常会用好些投影片,说明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细节。可惜,听众离去时,只是对这类学问印象深刻,但他们的生命却没有被摸着。在真正的解经讲道中,听众的「水平线」必须与经文的「水平线」融合[参附篇(一)中对迦达莫(Gadamer)的讨论] 。传道人必须问:倘若圣经的作者在向今天的会众讲道,他会如何应用这段经文的神学真理。 罗宾森(H.W.Robinson)将解经讲道定义为:「沟通圣经的一个观念,这个观念源于一段经文;在研究相关的历史、文法,与文学之后,靠着圣灵,传道人首先将它应用于自己本人,然后再传给听众」(1980:30)。这个定义非常好,兼顾到以上所谈的几个问题。现代的解经讲道者,第一步必须进入经文的原初状况中,然后再将原来意义的重要性,应用到自己身上。接下来才是把这些传给听众;而听众也必须先被带入圣经原初的情境中,然后才领受这些真理与他们个人需要的关系。许多时候,传道人只强调其中的一方面,以致讲道或是变成枯燥的解经,或是变成动力十足的娱乐节目。这两方面,就是经文原初的意义,和对我们时下情况的重要性,在解经讲道时都不可或缺,这才是释经学努力的真正目标。 结论 解释的过程包括十个步骤,本书将一一探讨(参图0.2)。诠释的研究可再分为归纳式(即我们与经文直接对应,自己得到结论)和演绎式(即我们与其他学者的结论对应,重新调整自己的发现)。归纳式的圣经研究,主要是将一卷书作图表和段落的分析,从宏观(全卷)和微观(段落),来判断作者信息的进展结构。结果是对经文的意义和思想过程,能有初步的概念。这一点很重要,因为此后我们便可以与解经的工具书(如注释书等)互动,而不至毫无批判地照单全收,只模仿其他人的观点(这是许多学生作业的通病)。 演绎式的研读使用第三至第六步,是解经研究中独立而又互赖的几个步骤。所有的工具--文法、辞典、字典、单字研究、地图、背景资料、期刊文章、注释--都要参考,以加深我们对该段经文的知识基础,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解开经文,不只停留在表面。藉着归纳法而得的初步了解,和与研究资料互动而产生的深度了解,使我们能对经文原初的含义作出最后的决定。 演绎法的一个主要功用,是使我们不用经文所用之字的现代意义来诠释它;因为我们对这些字有先存的个人经验,免不了会这样来解读。我们只能靠解经工具来做到这一点,因我们对古代的情形所知甚少,需要帮助。所以若要明了经文的「意义」,归纳法和演绎法都要一起使用。 解释任务的最后一步,是处境或神学的研究,让我们离开经文的意义(圣经的意思是什么),迈向处境的意义(圣经今天对我们的意思是什么)。「释经螺旋」不单出现在原初意义的层面--即沿着螺旋往上(透过归纳和演绎的研究)来明白经文的用意,也出现在处境的层面--即沿着应用的螺旋往上(由圣经神学至系统神学至讲道神学),能适切的明白这段经文对今日基督徒生活的重要性。圣经神学将个别经文与书卷的部分神学理论,放入以色列与初期教会的整体「神学」架构中(将两约整合起来)。历史神学研究教会在历史中如何将圣经神学应用于各样的处境里,以应对教会在历史发展各个阶段所面对的挑战与需要。系统神学将圣经神学重新架构,以因应当代出现的问题,并为那一代人总结神学的真理。最后,讲道神学(这个称呼是为了强调,讲道的预备本身也是释经任务的一部分)将以上所有步骤的成果,应用到今天基督徒实际的需要上。 图0.2本身取自尼达(Nida)和塔柏(Taber)对翻译过程的研究(1974)。这个理论主张,跨越文化的沟通理念,并不是直线的连续,因为任何两种语言或文化,都不可能衔接得如此紧密。「字面」法或一元法必定会造成沟通的错误。应当采用的方式为:将沟通的单位分解,成为「核心概念」,或基本声明,然后再运用收受文化的相对片语和思想模式,来将其重新陈述。在最基本的翻译一事上,固然要采用这个方式,而在诠释圣经的大范畴中,也同样必须如此行。解析圣经(文法、语意、文句结构)就是找出核心概念,而处境化的过程就是将其重新陈述,让同样的声音可以向现代文化说话。 读者将注意到,本书并没有将圣经文体的讨论放在最后(许多释经学的教科书都将它放在最后,视为「特殊释经学」),而是放在一般释经原则之后。因为文体主要关系到「它的意义为何」(经文原初的用意),理当在这里讨论。每一种文体都有「个案研讨」,将解析的原则应用在各种形态的圣经文学中。 读者也会注意到,我在全书中大半采用英语化的希腊文与希伯来文,只有第二章讲文法时例外。我的编辑们和我本人都认为,这样能帮助不常使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人明了讨论的过程,也许亦可学到与单字相关的事。第二章既是探讨技术层面,便要求读者能够运用原文;所以那里只用希腊文与希伯来文的原文。 |
 |
要认真研究圣经,第一步就是要衡量一段经文所处的整个情境(译注:在本书中, context译为情境、处境、上下文等)。倘若没有掌握整体的情形,就进行分析,这样开始的第一步,就注定其解释必不准确。离开情境,话语就失去意义。如果我说:「你的一切都要拿出来给它。」你一定会问:「『它』是什么意思?」「我要怎么作?」若不说明所处的状况(situation),这个命令就缺乏内容,变成毫无意义。在圣经中,上下文提供了经文所处的状况。
在研究圣经的时候,有两方面必须先行考虑:历史情境与逻辑情境。第一个范畴,就是研究该卷书导论方面的资料,以判断该书所面对的状况。第二个范畴,是用归纳法来追踪一卷书的思路发展。在仔细分析一段经文之前,这两方面都必须弄清楚。历史与逻辑情境提供了骨架,一段经文的深刻含义必须建立于其上。若骨架不强,解释的建筑必然会崩塌。
历史情境
一卷书的历史背景资料,可以从几种资源取得。最容易到手的,就是较佳注释书中的导论。许多这类注释书都有相当详细的摘要,说明各项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。最好是参考近日出版、研究深入的著作,因为最近数十年来资讯爆炸惊人。较老的著作不会提供令人兴奋的考古学发现,或近年有关圣经背景资料的新理论。旧约或新约导论也有很大的帮助,因为它们处理的范围较单卷的注释书更广。第三种资源为字典与百科全书,其中的文章不但讨论书卷,也讨论作者、主题,和背景问题。考古学与地图让我们能掌握一卷书背后的地志。像约书亚记或士师记等历史书,这方面的资料就非常重要。旧约或新约神学著作[如:赖德(Ladd)]常让我们明白单卷书的神学。最后,介绍圣经时期习俗与文化的书也很有价值,能澄清经文所特别强调之事的历史背景。
这个步骤是收集第二手资料,作为解释经文的准备(在开始解析研究的时候会用到)。从这些来源得到的资料,并不是最终的真理,却像一张蓝图,是基本的计划;当解释的建筑最后搭起来的时候,这个计画可能会更动。这些概念都是别人的,我们以后仔细研究,或许会得到不同的概念。这种预先研读有其价值,它使我们能远离二十世纪的角度,对于经文古代的情况产生更强的警觉心。在此我们需要思想几方面:
1.从某方面来说,作者的问题对历史批判研究比较重要,对用文法与历史来作解析,好像不太相关。可是,这一点仍然可以帮助我们从历史来看一卷书。举个例子,在研读小先知书的时候,我们必须知道阿摩司或撒迦利亚是在什么时候、向哪些人工作,才能明白他们话语背后的状况。了解他们的工作与背景,都会有帮助。好的导论能将一卷书的整个历史重现在眼前。这是极有价值的解释工具,因为经文乃是向原初的文化发言,若不进入那个文化,我们就无法有正确的了解。
2.写作日期也是一种解释的工具,使读者能解开经文的含义。如果但以理书是在马加比时期写的,它的意思便截然不同。倘若提摩太前书是在第一世纪下半叶,由保罗的一位门徒所写,它的色调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雅各书是写给西元一一O年之后分散的团体〔如:狄比流(Dibelius)的理论〕,它的解释也会不同。对这三个问题,我都持传统立场,这立场与我对经文的解释密切相关。启示录的时间,放在尼禄作王时(Nero,西元60年上下),和多米田作王时(Domitian,西元90年上下),在象征的解释上会有很大的区别。
3.经文的对象,在文意上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他们的境遇决定了该卷书的内容。当然,这个问题在新约更重要,因为旧约的作品总是写给以色列人的。然而,先知书背后的状况(例如以赛亚时代全国的情形)深深影响这些书卷信息的了解。希伯来书究竟是写给犹太人,还是外邦人,或是混合的教会,在解释上的确有区别。事实上,最后一类人的可能性最大,不过信中谈到的是有关犹太人的问题。几年以前,福音神学社收到一份彼得前书的论文,作者假定该书信是写给一间犹太人的教会。有人问他,如果收信者中有犹太人,也有外邦人,对他的论文会有什么影响;他必须承认,这一点会改变他整个论文。而事实上,彼得前书的对象的确是混合的会众。
4.在这四方面中,目的和主题对解释最有帮助。在研读任何一段经文的时候,我们对于该卷书面对的问题和环境,都要有基本的知识,也要知道作者是用什么主题来谈这些问题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约翰在第一封书信中,是面对诺斯底派刍形的挑战,就很可能误解约翰壹书一章8-10节护教的语气。直到最近,注释家才开始研讨个别书卷的圣经神学。可是这是极有用的解释工具。倘若注意到一卷书的整体观点,对于其中个别声明的解释,就更容易准确。如果明白路加的重点是救恩(历史),同时他也强调一些主题,诸如圣灵、敬拜,和社会关怀,对了解其中的比喻--如财主与拉撒路(路十六)--会有很大的帮助。
从这些来源所得到的资料,可以作为一种过滤器,将个别经文在其中滤过。在详细的解析与研读经文之后,这些预备资料或许会需要修正。它的目的是将解释的定律规范得更窄一些,让我们所提的问题更恰当,强迫我们回到原初作者的文化,以及经文背后当初的状况中。这样,我们就不至于将二十世纪的意义读入第一世纪的用语中。这种方法让人事先进行了解,将经文与背景衔接起来。同时,这些资料必须摆在经文面前,不要放在它背后;也就是说,在我们仔细研读个别段落时,或许会需要修正它。这份材料绝不可以勉强经文跟随它的指引,因为它是次要的,而主要的知识必须经由研读经文本身而来。
逻辑情境
实际来说,逻辑情境是解释最基本的要素。我告诉班上的学生,如果有人打瞌睡,没有听到我问的问题,而倘若他/她回答「情境」,可能有一半答对的机会。这个词本身对经文的影响是一系列的。最佳的图解方式,就是一连串的同心圆,以经文为中心,向外扩展(参图1.1)。
愈靠近中心,对经文意义的影响力愈大。例如,辨认文学形式的风格,可以帮助诠释者认出何为比喻,可是这一点比不上其他经文对该段经文的影响力。比方说,我们可以辨识出启示录是启示文学;虽然两约之间与希腊式的启示文学都可以提供重要的类似处,但是启示录大部分象征乃是取自旧约。从另一端来看,一个词汇或观念的意义,最后的仲裁者为其直接的上下文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中用的词,与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中的用法,不保证一定相同。因为语言的运作本来就不是如此;每一个字都有许多含义,作者的用法要视当时的上下文而定,与前一段中的用法无干。aphiemi一字是很好的例子,在约翰福音十四章27节为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」,而十六章28节则为「我又离开世界」。这两者不能互相解释,因为它们的用法正好相反。在第一处,耶稣给门徒一样东西;在第二处,他则是将一样东西(他自己!)从他们当中拿走。而「赦免」一字,我们更不能按平常的用法来理解(如:约壹一9)。其他经文能帮助我们了解语意学的范围(这个字可能有的不同含义),但是惟有当时的上下文足以限定可能性,指出其实际的意义。
图1.l也将以下几章包括在内。一般所谓的「归纳法查经」包含几个层面,就是将整卷书作图表,和分析一个段落。归纳法一般是指个人对一段经文专心的研究,不使用其他工具书(如注释书)或资料。我直接进入经文,对它的含义自己下结论,而不是借用别人的结论来了解。这种掌握批判力的方法,使我在必须用注释书和其他材料进一步深入研究经文时,不致过分受到它们的影响。我必须先有定见,再与其他人的结论互动。否则的话,我只是复述别人的意见而已。现成的资料带我进入经文背后的状况,而我自己归纳式的研读,使我能预备好资料,来评估各种注释书。
1.整体的研读:一卷书的图解。过去十年中,文学批判对圣经学界作出了很宝贵的贡献。在那之前,因着形式批判的影响,研究重点都放在单独的段落,不注重整体;学者将各卷书拆散,成为各自独立、互不相干的部分,然后才分析其意义。注释书因为过分强调单字的研究,使这种不平衡的趋势更加恶化,甚至字与字之间都显得没有什么关联。然而,文学批判却指出,除非从整体来看,否则各部分就没有意义。惟有先顾及整体,然后才能针对其中各部分、按着中心信息来研究。实际而言,释经的过程可以简述如下:第一,将整本书作成图表,初步分析它的思路流向;接下来,专注于每一部分,察究论证的细节;最后,再重新调整全卷的思路发展,使其与各部分息息相关。
阿德勒(Adler)和范道伦(Van Doren)合写的名著《如何阅读一本书》(How to Read a Book,1972:16-20),探究阅读的四个阶段:(1)初步阅读,重点在辨认其中的用词和文句;(2)调查式阅读,就是综览全书,找出基本的架构和主要思想;(3)分析式阅读,对全书作深入的研究,尽可能彻底明白其信息;(4)同类式阅读,即将所得的信息与其他类似书籍作比较,对主题作出第一手的详细分析。前面两个阶段是归纳法,后面两个则是以研究为取向,不单用到原来的文字(原著),也用到次要文字(对该书的解释,或其他人所写相关的书)。
本章要探讨调查式阅读法。阿德勒和范道伦将这个方法分为两个途径(1972:32-44)。第一,翻阅介绍部分(序言、目录、索引),并浏览主要的篇章与段落,以明白全书基本的进展与中心思想。就圣经的一卷书而言,这就包括前言与各段的标题(如果用研读本圣经),再加上熟读重要的几章(如:罗-、三、六、九、十二)。第二,速读全书,不要停下来思想个别的段落或难明的观念。这方式使我们可以明白并记住全书的要点,不致立刻迷失在一些细节中。
我要将这种调查式阅读法的范围再扩展一些,把结构发展也包括在内;我称之为「书卷图解法」(Osborne and Woodward 1979:29-32)。这时候最好用一本分段良好的圣经。我们必须记住,章节并没有被默示。事实上,是直到一五五一年圣经才分成节,有一位巴黎的出版商,名叫司提番那(Stephanus),他用了六个月将全本圣经分成节,然后出版了他最新的希腊文版。根据传说,司提番那是骑在马背上作这件事,而他分节的依据,是马行进时对他笔的震动!后来司提番那的版本普及各处,没有人敢擅自更动,而他的分法一直沿用到如今。问题是,司提番那对章节的分法常有问题,可是一般人以为他的判断乃是正确的,以致在解释各章各节时,没有顾到上下文。所以,我们在决定意义时,绝不可倚赖节的区分。分段乃是了解各卷书思路发展的要诀。
我教导教会团体查经法,时常发现,对初学者而言,最困难的事就是速读每一段,写下重点。大家很容易一头栽进细节,却不懂得鸟瞰全章。在这一步,我们需要从整体来看,学生应当学习用六到八个字来作每一段的摘要。如果我们读得太细,摘要就会只反映出全段的前几节,而不是整段。这种错误会使整个研究有所偏差。在图1.2和1.3中,我用约拿书和腓立比书作例子,以说明这种方法在旧约和新约中都可使用。
如约拿书的图解所示,按照顺序,以简短的话囊括每一段,只要顺着摘要看,就可以感受到全卷的思路。而综览整个图解,全书的轮廓便一清二楚。例如,我们很容易看出,第三章成就了第一章原初的目的,就是到尼尼微的使命,以及百姓的悔改。因此,全卷有两处平行,第一与第三章,第二与第四章。再者,重点为后一个平行,因此约拿书的要义不在于宣教,而在于约拿(和以色列)对神的态度,和对神要怜悯之人的态度。第四章是「故事的精髓」,教导神的怜悯。
| 第一章 | 第二章 | 第三章 | 第四章 |
| 1-3 传道的命令;违逆与逃避 | 1-5 祈祷;约拿的痛 苦 | 1-3上 二度命令;约拿顺服 | 1-4 约拿发怒;神发问 |
| 4-12 神的风暴;水手的惧怕 | 6-9 祈祷;约拿的信心 | 3下-9 传道与尼尼微 的悔改 | 5-8 神的教导(1):蓖 麻枯萎,约拿发怒 |
| 13-16 水手顺服,抛 约拿入海17 大鱼吞约拿入腹 | 10 被吞出 | 10 神的赦免 | 9-11 神的教导(2):神的怜悯 |
| 第一章 | 第二章 | 第三章 | 第四章 |
| 1-2 问安 | 1-4 合一与谦卑,不自夸 | 1-4 警告犹太派 | 1 站稳 |
| 3-8 感恩:为相交与分享 | 5-11基督谦卑与高升的榜样 | 4下-6 保罗辉煌的资历 | 2-3 祈求合一 |
| 9-11 祈祷:为他们的爱心和分辨力 | 12-13 责任与神赐的 能力 | 7-11 为基督看一切为 有损 | 4-7 劝勉:喜乐、温柔、为挂虑祈祷 |
| 12-14 他的囚禁使福音广传 | 14-18 作见证,不埋怨、不相争 | 12-14 竭力更多得着基督 | 8-9 思想美事并且去行 |
| 15-18 因敌人播扬福音而欢喜 | 19-24 称赞提摩太真正的关心 | 15-16 听从的呼吁 | 10-13 喜乐与满员,因他们的分享与基督的预备 |
| 18下-26无论得释或殉道都将欢喜 | 25-30 称赞以巴弗提不顾性命 | 17-21 真假教师的对 比 | 14-19 喜乐与满足进一步的解释 |
| 27-30 虽遇逼 -/迫仍然同心合意 | 20-23 颂荣与最后问安 |
如果我们将第四章定为「约拿的忿怒」或「忿怒得回答」,就会错失了要点,即:约拿学到了神赦免的意义。所以,每一段标题都必须抓住该段的要义。不过,我们也必须记得,这只是预备性的综览,在仔细分解之后,若有需要变更之处,还要修改。像约拿书或腓立比书的长度,作综览大约需花四十到四十五分钟。
现在让我们更深一层,一步步探索如何制作图解。
一、速读段落最有效的方式,是拿一枝笔。一面读,一面写下摘要。这样作最能专心。速读一段经文(或稍为仔细去读),最大的问题是心思不集中。我常发现,读完一段之后,我的心却在想当时面对的问题,或当天要作的事,结果必须重读一遍(有时几遍!)。如果我边读边记,强调第一印象,就比较能专心。还有,如果以一句话作摘要嫌不足,我就抓住那段思路的进展(如,腓四4-7一连串的劝勉;见图解)。这时,速读并写笔记的方法便有助益。这步骤的价值为:所作的图解成了地图,可以追踪整卷书的走向。以后再仔细研读各个段落时,我可以一眼就断定某句声明前后的思路。
二、在图解全卷之后,就可以回头检查,寻找全书各段中思路进展的模式。如果发现段落之间思路中断,就应当用单线作记号(参上图)。内容类似的段落组成全书的大段,这样便能看得更准确。有些思路的改变很容易看出,如从保罗对自己的评语(一12-26)转为论腓立比的情形(一27-28),或进一步从腓立比人的情形转而称赞提摩太和以巴弗提(二19-30)。有些改变则不太容易察觉,如从谦卑的提醒(二1-11)稍微转向警告(二12-18),或将四章1节与三章17-21节相连,而不与四章2-9节相连。至于最后一点,读者暂时只能猜测原因,等到仔细解析全书之后,才能完全澄清。
这就是我为何将约拿书和腓立比书都放在这里的原因。约拿书是圣经中大纲与章的分段符合的少数几卷之一,可以成为简单的范例。约拿书中惟一的问题,是一章17节究竟是第一章的结论,还是第二章的引言。腓立比书就复杂得多,需要更仔细的思想。它是教导式的题材,不是故事或叙述(如约拿书)。这类文字的分段常较突兀(如二25-30,三l-6),全书的进展也不容易确定。不过,这两个例子的作法,都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整卷书的思想进展。
另外一个困难,是找出模式改变的方法。虽然圣经每一段的组织都有意义,但思想模式却常不容易辨识。司陶特(D.Stuart)说:「模式的分辨,在于寻找一些主要的特点,诸如发展、继续、独特的片语形式、中心或枢纽的字、平行、交错、含括等重复或进展的模式。模式的要诀常是重复与进展」(1980:36;强调字为原书所有)。华德·凯瑟( W.Kaiser)提供了更详细的说明,列出八个发掘思想单位「缝合处」的「线索」(1981:7l-72):
1.重复的名词、片语、子句,或句子,可以成为标题语,引介各个部 分,或成为末尾的结语,结束每个段落。
2.文法常可提供线索,如转接性的连接词或副词;例如:「后来、所以、为此、但是、然而、同时」,和希腊文的oun,de,kai,tote,dio。
3.修辞式的问话常代表转向新的主题与段落。这类问题有时相连成串,将整个论证或一个段落往前带动。
4.时间、地点,或背景的改变,是一种常用的技巧,表示新主题与段落的出现;尤其是在故事中。
5.称谓的改变,通常特意显示:注意力已由某个团体移到另一个团体;这是最重要的技巧之一。书信式的文字中经常使用。
6.动词的时态、语气等的改变,甚至主词或受词的改变,也可能是新段落的线索。
7.钥字、命题,或概念的重复,暗示出一个段落的范围。
8.偶而,一段的主题会在该段的标题语中出现。在这种特殊状况下,诠释者只需要确定:该段所有的内容都包括在作者明示的目标之内。
在我们速读各段、写摘要时,这些基本的模式中断方式颇有帮助。既知道这些可能性,在制作图表的时候,就可以判断思路的转折。甚至在作更详细的解析时,这些中断方式也有用处。
三、最后一步,是再将各段区分成大单位,以双线来表示。教导类的书卷,如腓立比书,这样做格外有价值。这个过程与前一步差不多,可是思想的单位比段落更大,乃是建造在第二步之上。作完这个步骤,把结果与我们所收集的注释书和导论比较一下,颇有帮助。我们甚至可以将结果记在图上[例如,将注释者的名字,如Ralph Martin(丁道尔系列的腓立比书注释)或Gerald Hawthorne(Word系列的腓立比书注释),放在他们所认为该分大单位的所在〕,以作比较,在未来的研究上可以指引我们的思想。不过,最重要的是,一开始我们要自己作归纳研究,未完成之前,千万不要去查阅第二手资料。否则我们一定会被其他人的看法控制。归纳法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关卡,使我们不致盲目随从注释书,可以找出自己的解释,不致像鹦鹉学舌一般,只是重复某些专家学者的意见。
然而,这个方法对诗篇与箴言并不适用(个别的诗篇或许可以使用,但是整卷却无法采用)。虽然许多人尝试将诗篇用不同的方法分类,但是以主题来架构的模式太过肤浅。箴言也相仿;直线型发展的部分(如第一-九章,或三十一章)可以用图解,但是箴言的收集部分,却无法从整体的角度来研究(参本书第七、八章)。
再者,或许有人会问,这个方式对很长的书卷(如以赛亚书或耶利米书)是否适用?这个问题问得有理。虽然长书卷的图解比较难,但是我衷心相信,这样作很有帮助。容我用一卷书作例子。这卷书不算最长,但却是圣经中最困难的部分之一,那就是启示录。我不作整个图表(请读者自行尝试),而是讨论其结构的暗示(第二、三步)。我们在经文里面寻找模式时,可以看出启示录的组织是天与地之间循环出现。只要浏览图解,就会看到第一、四-五、七(十)、十四-十五,和十九章l-10节是天上的情景,而第二-三、六、八-九、十一-十三,和十六-十八章是发生在地上的事。结论部分(十九11-二十二2)则将天与地结合起来。此外,在这个轮转的模式中,天上的景象主要是赞美与敬拜,而地上的景象则是愈来愈混乱、痛苦,神的审判也愈发加重。这个模式最佳的证明,是印、角,和碗的关系。用归纳法的表,我们可以看出,它们的组织模式是相同的。因此,印、角,和碗乃是以循环来组织,特色是审判与毁灭的逐渐加强(受影响的程度,六8为地的四分之一,七7-8为三分之一,十六3-4为全地)。天上与地上景象的对比,指出全书具合一的主题,即神的主权(垂直方向),并导致水平方面,就是要求教会信靠神,无论目前与未来的苦难为何。
我要再度强调,这只是初步的大纲,还不是最后的。它代表读者的观点,但不一定是原作者的看法(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)。迈尔(Meyer)和莱斯(Rice)(1982:155-92)举例说明,读者的角度会如何影响一段文字的组织图,不过他们承认,「读者的任务……是建立自己对该段文字架构的了解,并使这架构尽量接近作者的原意」(p.156)。他们的实验小组研读一段有关铁路的文章,来显示个人的角度如何影响对文章结构的看法。当然,因为每个人的期待不同,对经文架构的分析就很不一样。我们必须承认,自己的前提很容易影响对经文的看法。在归纳法的过程中,读者扮演关键性的角色,而若要明了作者原初的设计,就必须更进一步研究。然而在解释的过程中,归纳法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,因为它能够提供观点。
2.部分的研读:段落的图解。若要像解析较大的单位(一卷书)一样,来图示较小的单位(段落),垂直图比前述的水平图更好用,因为单位小。对不熟悉原文的人,我推荐使用新美国标准圣经(NASB)来进行这一类研究。这个译本虽不如其他译本流畅,可是它对直译十分讲究,因此最接近希伯来文或希腊文,让我们更清楚看出圣经作者原初的写作模式。图解的样式可以有几种(我们将用弗一5-7作实验)。许多希腊文解经课都使用复杂的图解(参图1.4),每一个词都要放在它所形容的字底下,两者的关系也要说明(参Grassmick)。费依(Gordon Fee 1983:60-76)提出句子流程解析图(图1.5),和文法分析图类似,但没有那么复杂。两者都将主词、述语,和受词放在一页的左角,而将附属词汇缩排,放在所修饰的字或片语底下。费依建议用注解来说明文法的判断,而用颜色来标示重复的字或主题。



我喜欢较简单的方块式图解(图l.6),过于字或片语的图解(图1.4和1.5),因为它可以表达子句的层面,较能呈现全面性。另外两个方式将每个字或片语都作图示,而方块图解只图示主要与次要的子句(或长片语)。这三种图,在层次上一个比一个广--字、片语、子句;而子句则是一段话的大块结构。方块法有一些缺失;例如,它不像另外两个图那样能表达细节。然而,它有三项优点,足能盖过其缺点:(1)它比较简单,花的时间较少;忙碌的牧师或平信徒能够持续使用;(2)在子句结构中,大部分其他关系(诸如形容词、名词的修饰语、副词,或修饰动词的介系词片语)也能显示出来;(3)句子图解的目的,是将一段经文的思路以一目了然的方式表达出来,而不是要深究文法的细节。另外两种方式,对于目视太过复杂,无法达到这一点。在解析研究中(第二至五章),文法的细节会显露出来,可是在这样的初步阶段,讲究细节不但无助,反而有损。文法最好留到以后的过程再考究。此外,在下面的解析过程,图解就不那么重要,因为是要澄清句子当中的细节,而不是要目视思想的流程。所以,句子图解已经足以达到我们的目标,不需要详细的文法图解。
在句子图解中,首先要作的,是区别主要子句与次要子句。我们的教育体制很少讲到这方面,实在让人讶异。在希腊文课上,我常问学生,他们最后一次上文法课或句子解析课是什么时候,大部分人从初中之后就再没有接触;有几位主修英语的学生,在大学里面也完全没有碰过!因此,我们不得不承认,我们对这方面的知识非常缺乏。
子句乃是句子中含有主词与述词的部分,例如,「我看见那个男孩」(主要子句)或「因为我看见那个男孩」(附属或次要子句)。以上两句的分别为:第一句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句子,而第二句却不能。在第一次读圣经的句子时,我觉得最好的办法,是向自己大声念出每一个子句,看看哪一句为不整全的句子,哪一句可以独立。
例如,腓立比书二章6节(参以下图解)。我还是喜欢用直译式的译本,如新美国标准圣经,因为它比较接近希腊文和希伯来文,在研经上有好处(当然,懂得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的人,可以直接用原文圣经)。腓立比书二章6节的经文为:「那位(Who),虽然他曾以神的形像存在,(却)不以与神同等为一件要抓紧的事。」这里的「那位」引进二章6-11节的道成肉身伟大赞美诗,因此当视为名词(第5节的「基督耶稣」)。我们开口读这一节,就会发现,「虽然他曾以神的形像存在」,本身并不能独立为一句话,所以它是主要子句(「他……不以与神同等为一件要抓紧的事」)的附属子句。作图解时,我们将次要子句缩入半寸左右,并用箭头指出它要修饰的子句。
虽然他曾以神的形像存在
那位……不以与神同等为一件要抓紧的事。
许多人喜欢将修饰子句缩排在所形容之字的下面。这方法在视觉上效果不错,可是我感到它颇难使用。许多附属子句是修饰一个子句的最后一个字,用这个方法会占用很多空间。此外,保罗很会用回旋式句子,例如,以弗所书一章3-14节就是一句话,其中的结构复杂得不得了。用这种方式图解,一张纸绝对不够,需要用八尺宽的纸!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是缩入半寸,并将箭头放在要修饰的子句底下。
在方块图解中,有几方面需要注意(图1.7)。第一,箭头要指向所修饰的词,而附属子句或片语比要修饰的子句缩进半英寸。第二,缩排子句经常会一连串,因为会有次要子句修饰另一个次要子句的情形。这就是句子图解的主要价值所在,因为它可以使这种复杂的关系一目了然,增进我们对思路进展的了解。第三,平行子句或片语要以箭头(如果它们是附属的,如以上弗一5-6的两个介系词片语)或直线(如果它们不是附属的,如第7节的两个名词)相连。以弗所书一5-7有四个连续的附属关系。倘若我们以横接的方式来写,需要很多空间;而用箭头,就简单又有效。箭头也使我们能顺着经文的顺序,避免搞混。次要子句若在前面,箭头就朝下(参以下腓二6的图解),若在后面,箭头就朝上(如以上弗一5-7)。
在圣经中辨认子句最有效的方式,也许是研究连接的字。对圣经研究而言,这一点尤其真确,因为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经常使用连接词。我们必须问,它是否为对等连接词(以及、但是、可是、既…又…、不但…而且…、不是…就是…、因此、因为、于是)--衔接平行句或主要的子句,还是附属连接词(除非、之前、之后、同时、当时、自从、因为、即、如果、虽然、虽、以致、为要、除外、如同、那么、那里)--衔接修饰子句。
我们也可以陈明附属的关系,就是用一些记号来代表各种语法关系(如,T代表时间[temporal],Ca代表原因[causl],Cn代表让步[concessive],Cd代表条件[conditional],R代表结果[result],Rel代表相关[relative],P代表目的[Purpose],Me代表媒介[means], Ma代表方式[manner], I代表工具[instrumental])。这些记号可以写在箭头旁边,如此,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段经文中附属子句的模式。我要以腓立比书二章6-11节整首道成肉身的赞美诗来作图解示范(参图1.7)。
这个图使人一眼看出,主要的两段是耶稣的行动和神的行动。在前者之下有三个基本概念:耶稣的顺服、倒空和谦卑。在后者之下只有一个主要概念--神升高的行动--以及两个次要概念--万膝都要跪拜和万口都要承认。我们会立刻注意到,这可以成为初略的讲道大纲。事实上,方块图解可以成为讲章或查经的初步纲要。在查看图中的子句模式时,也可以马上看出哪些是主要子句,哪些是次要子句(正如我们在腓二6-11所见)。
不过,在此要提出两项警告:第一,大纲就像图解一样,乃是初步的,仔细解析经文之后,可能需要更改。第二,句法的关系固然对判断思想的主要部分很有帮助,可是却不能自动作出判断。子句常有平行现象(如7-8节的倒空与谦卑,或10-11节的跪拜与承认),必须结合成为一个要点。还有一件事也很要紧,有时在作者的实际思想发展中,文法上的附属语和主要子句同样重要,甚至比它更重要。保罗在这方面最出名。如果附属概念有详尽的说明,就是一个记号,表示作者认为它是要点。例如,腓立比书二章2节说:「要有同一个心思、同一份爱、在灵里合-、心思朝向同一个目标,使我的喜乐满足」。显然,这里最要强调的并不是使保罗的喜乐满足,而是腓立比
教会的和谐;连续四个附属子句说明了带给保罗更大喜乐的途径。在讲道大纲中,要点应当是和谐,而不是喜乐。同样,在腓立比书的赞美诗中,保罗用了两个附属子句来修饰倒空(7节)和谦卑(8节)显示保罗实际上是在强调道成肉身的事(「成为人的样式」)。
传道人应当从直线图发展出讲道大纲。最佳的方法,是将它与图并排,对照重点。在这个步骤中,讲道大纲就像查经材料一样。可是我在十五章中会提出,在一篇解经讲道中,经文应当主导其架构。如果我们主控经文,勉强它来配合自己预先想好的信息,就不是在传讲神的话,而是在分享我们的想法。当然,有时候这类信息(专题式)有其必要,不过它不算真正的解经讲道。所以,大纲必须配合经文的架构:
一、谦卑的光景(二6-8)
1.心思的光景(6节)
1)他的本体
2)他的决定
2.存在的光景(7-8节)
l)他的道成肉身(7节)
a.他的本体
b.他的形像
2)他的谦卑(8节)
a.他的样式
b.他的顺服
二、高举的光景(二9-11)
1.被神高举(9节)
l)他的新地位
2)他伟大的名
2.被人和万物高举(10-11节)
1)藉服从来高举(10节)
2)藉承认来高举(11节)
a. 宇宙性
b.内容
c.结果
这仍然只是初步的大纲,要等到解析全部完成后,才能定案。到那时候,经文可以转变成满有动力的讲道模型(参本书第十六章;Liefeld 1984:115-20)。不过到目前为止,我们对腓立比书二章6-11节的研读非常有意义,不但作出了未来查经或讲道的大纲,也提供了可能的信息。除了本段之外,只有约翰福音一章 l-18节对道成肉身和基督的高举有如此深刻的神学反思。在前半段中(6-8节),三个主要子句都提到道成肉身的时刻。第一处是从负面来讲,耶稣拒绝神性的特权与荣耀(6节);接下来是从正面来谈倒空与谦卑,耶稣将他的人性(「奴仆的形像」,7节,与8节相较)加在他的神性(「神的形像」,6节)上。这种仆人基督论,成为基督徒行为的模范或准则(注意5节),高举的段落(9-11节)因此更显得动人。我们若像基督一样「谦卑自己」(与3节比较),神就必将我们高举,分享基督的荣耀。当然,我们并没有「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」。但是,约翰福音十七章22节的平行句,在此颇有帮助: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,我已赐给他们」。若分享耶稣的谦卑,就将分享他的高举。
我要再用一段旧约经文来说明这个方法。请看以赛亚书四十章27-31节。首先,我们需要明白这段圣经背景的大环境。第四十章是以赛亚书第二大段(四十-五十五章)的开始,其中心为「仆人之歌」,与神对列国普遍救赎的爱。这开头的一章是一首奇妙的赞美诗,颂扬神的全能与救赎的爱。后半段(18-31节)为一连串修辞式的问题,责备以色列缺乏信心。神无可比拟(18-20节)、无限伟大,远超地上或天上的一切荣耀(21-26节),他会为他的子民行事(27-31节)。
你为何说,哦,雅各
并肯定,哦,以色列,
我的道路向上主隐藏
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?
你不知道吗?
你未曾听过吗?
永在的神,上主,地极的创造者
并不疲乏或困倦。
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
他赐力量给疲乏的,
又将力量加给赐缺乏能力的。
即使少年人变得疲乏困倦,
强壮的年轻人全然跌倒,
但那等候上主的将得着新的力量:
他们将如鹰展翅上腾,
他们将奔跑而不困倦,
他们将行走而不疲乏。
我们首先会注意到,旧约经文缺乏附属子句。由于希伯来文不太使用连接词,图解的帮助便不像新约那么大。类似这样的诗体经文,大半都是主要子句。在散文中,主要的连接词(即「以及」)子句占多数。所以,我们必须寻求修辞的模式,并注意思想有否改变。在这时候,直线式的图解仍有帮助,因为他将句子并排在一起。这一段中,我们立刻注意到,思想是以对句出现。每一个概念都重复强调。并且,在引介的问题之后,有一种ABA的模式。第一组对句是以神为中心,讲到神是怎样的一位(28节下),他怎样赐予有需要的人(29节)。中间的对句(30节)将神的子民与强壮的战士作对比,这些人也会力量衰竭;最后一组对句(31节)说明等候上主的结果。初步的研究大纲可能如下:
前言——神义论的问题(27-28节上)
一、神会行动( 28下-29节)
1.他是怎样的一位(28节下)
2.他会做什么事(29节)
二、接受他的能力(30-31节)
1.没有接受的人(30节)
2.接受的人(31节)
另外一种可能,是将第30节作为第二大点,第31节作第三大点。当我们研究思想模式时,有一件事立刻会让我们吃惊:这三段都是采用运动或军事的意象,尤其是奔跑与困倦的衔接。神绝不会困倦,年轻的运动员却会;凡信靠神的人会得着他的力量,得着奇妙的坚忍力量。这样的一段经文显然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。3.弧形法。富乐(Dan Fuller)发展出一种新方法来图解一个段落(或一卷书),他称之为「弧形法」(他在富勒神学院教释经学的讲义第四章,未出版)。这方法的前提与方块图解相同,但是他以水平的方式写,而不用垂直的方式,从许多方面看,他对视觉的效果更好,更容易捕捉思想的发展(参图1.8)。相关的子句以弧形相连,并注明其关系,然后整个单位再加上弧形,并注明关系。从这种图,我们很容易察觉一个整体中的重点与次要之点,也能够准确指出各部分的关系。
每个人最好能发展出自己的关系表与钥字;不过,除了前面的表(参上文)之外,我还要提出一些连接子句的缩写方式:Adv代表反义词[adversative]、Pr代表进展[progression]、S代表系列[series]、Co代表比较[comparison]、Wh-Pts代表整体一部分[whole-Parts]、Id—Int 代表概念-解释[ide—ainterpretation]、QS-AS代表问题-答案[question-answer]。至于附属关系,用Inf代表推理[inference]、Loc代表地点[locative,“in”]、 G代表根基或基础[ground]。这些记号的价值,是一眼就能看出思想的发展。我个人建议,保罗(以及新约几位作者)比较繁复的句子,用方块式图解,这是垂直模式中视觉较佳的方式;而旧约的平行子句最好用弧形法,因为方块图解的价值不大。
事实上,若将弧形法用在保罗书信,以弗所书一章5-7节就可以显出一个问题。第5节很不容易用弧形来表达,因为三个介系词子片语都修饰主要的子句,而不是互相修饰。用弧形法,看来会像它们在彼此修饰,但其实它们只修饰主要子句。不过,这种视觉模式仍十分有用。
作一段经文的思路结构图解时,常会碰到修辞学的技巧,也就是传达信息的文学方法。这便是概念的第三种情境,也是它的最后一个层面;这三个层面分别为:全卷书组织模式的宏观层面、分段的中间层面,与各段之内的写作技巧。以下四章所要探讨的题目,就是这种微观的层面(经文用字的详细结构)。
我们可以参照亚里斯多德(Aristotle)对修辞学的古典定义:「它是讲究如何以最佳方式说服人接受某个思想的艺术」(Kessler1982:2)。修辞学的研究,常与形式(文体)和功能(组织技巧)混为一谈。修辞学最古典的四种分类为西塞罗(Cicero)所定,即:虚构、编排、体裁,与记忆的技巧。风格并不在这些范围之下,因为按定义而言,「修辞批判」(rhetorical Criticism)主要是在谈沟通的技巧,换言之,就是谈作者表达论点的技巧与组织模式。克斯乐(Kessler 1982:13-14)主张,在修辞的分析中,最重要的乃是与历史无关的一面--亦即,与经文本身相关的一面。在本段中,我采用这个观点来看经文的结构,并探究圣经作者(及其他人)用什么文学技巧来串联他们的论点(其他类型的修辞批判,参第四章的附注)。
概念或思路之间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关联。但是要详细分类,却有困难。我的办法是把迈尔和莱斯,以及尼达等人的努力结合起来。这种分类相当重要,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研究圣经中个别的结构;对这些形式若有基本的了解,在研读不同段落的时候极为有用。所以,我将用圣经的例子来说明每一种修辞方式。 3.比较(comparison)是显示概念的相似之处或差异之处。最著名的例子是罗马书五章12-21节,亚当与基督的对比;两者都为一群人的代表(注意15节的「一人」与「众人」),或是有罪的人,或是基督徒。我们也可以举罗马书七章7-13节(过去式)与七章14-25节(现在式)两种关系的辩论为例。究竟这两段是讲未重生到重生的状况,还是过去的以色列到现在的以色列的状况(Moo 1986),我们必须作一判断。另外一个著名的对比是约翰所用的光与暗,在约翰福音一章 5节,三章 19节,尤其是八章 12-九章41节。其背景为宇宙之战,而黑暗不能「胜过」光(一5),在我们遇见基督--「世界的光」--时(八l2-13),则还有小规模的战役。箴言亦有许多智慧与愚昧相对的话,如一章7节,十五章5节等(参本书第七章有关箴言的解释)。 1.整体的研读:一卷书的图解。过去十年中,文学批判对圣经学界作出了很宝贵的贡献。在那之前,因着形式批判的影响,研究重点都放在单独的段落,不注重整体;学者将各卷书拆散,成为各自独立、互不相干的部分,然后才分析其意义。注释书因为过分强调单字的研究,使这种不平衡的趋势更加恶化,甚至字与字之间都显得没有什么关联。然而,文学批判却指出,除非从整体来看,否则各部分就没有意义。惟有先顾及整体,然后才能针对其中各部分、按着中心信息来研究。实际而言,释经的过程可以简述如下:第一,将整本书作成图表,初步分析它的思路流向;接下来,专注于每一部分,察究论证的细节;最后,再重新调整全卷的思路发展,使其与各部分息息相关。 2.文法常可提供线索,如转接性的连接词或副词;例如:「后来、所以、为此、但是、然而、同时」,和希腊文的oun,de,kai,tote,dio。 3.修辞式的问话常代表转向新的主题与段落。这类问题有时相连成串,将整个论证或一个段落往前带动。 4.时间、地点,或背景的改变,是一种常用的技巧,表示新主题与段落的出现;尤其是在故事中。 5.称谓的改变,通常特意显示:注意力已由某个团体移到另一个团体;这是最重要的技巧之一。书信式的文字中经常使用。 6.动词的时态、语气等的改变,甚至主词或受词的改变,也可能是新段落的线索。 8.偶而,一段的主题会在该段的标题语中出现。在这种特殊状况下,诠释者只需要确定:该段所有的内容都包括在作者明示的目标之内。 2.部分的研读:段落的图解。若要像解析较大的单位(一卷书)一样,来图示较小的单位(段落),垂直图比前述的水平图更好用,因为单位小。对不熟悉原文的人,我推荐使用新美国标准圣经(NASB)来进行这一类研究。这个译本虽不如其他译本流畅,可是它对直译十分讲究,因此最接近希伯来文或希腊文,让我们更清楚看出圣经作者原初的写作模式。图解的样式可以有几种(我们将用弗一5-7作实验)。许多希腊文解经课都使用复杂的图解(参图1.4),每一个词都要放在它所形容的字底下,两者的关系也要说明(参Grassmick)。费依(Gordon Fee 1983:60-76)提出句子流程解析图(图1.5),和文法分析图类似,但没有那么复杂。两者都将主词、述语,和受词放在一页的左角,而将附属词汇缩排,放在所修饰的字或片语底下。费依建议用注解来说明文法的判断,而用颜色来标示重复的字或主题。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 即使少年人变得疲乏困倦, 概念或思路之间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关联。但是要详细分类,却有困难。我的办法是把迈尔和莱斯,以及尼达等人的努力结合起来。这种分类相当重要,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研究圣经中个别的结构;对这些形式若有基本的了解,在研读不同段落的时候极为有用。所以,我将用圣经的例子来说明每一种修辞方式。 1.集合关系(collection relations,Nida:「重复」,Liefeld:「连续」)是按照要点相同的基础,将概念或事件连在一起。这是古代很常见的修辞方式。拉比称它为「串珠」,并常将弥赛亚的经文放在一起。这个方式可以说明希伯来书一章4-14节,这些串在一起的证明经文分别取自诗篇二篇7节;撒母耳记下七章17节;诗篇九十七篇7节,一O四篇4节,四十五篇6-7节,一O二篇25-27节和一一O篇1节。马太福音与五段讲论,也有类似的集合;例如,在使命讲论中的末世性段落(参太十16-22与可十三9-13)。有时,一些看似互不相干的系列,会以标示语相连。马可福音九章33-50节就是讲论奖赏与责罚的文集。这一段是围绕着「奉我的名」(37-41节)、「跌倒」(42-47节),及「盐和火」(48-50节)来组织的。 3.比较(comparison)是显示概念的相似之处或差异之处。最著名的例子是罗马书五章12-21节,亚当与基督的对比;两者都为一群人的代表(注意15节的「一人」与「众人」),或是有罪的人,或是基督徒。我们也可以举罗马书七章7-13节(过去式)与七章14-25节(现在式)两种关系的辩论为例。究竟这两段是讲未重生到重生的状况,还是过去的以色列到现在的以色列的状况(Moo 1986),我们必须作一判断。另外一个著名的对比是约翰所用的光与暗,在约翰福音一章 5节,三章 19节,尤其是八章 12-九章41节。其背景为宇宙之战,而黑暗不能「胜过」光(一5),在我们遇见基督--「世界的光」--时(八l2-13),则还有小规模的战役。箴言亦有许多智慧与愚昧相对的话,如一章7节,十五章5节等(参本书第七章有关箴言的解释)。 1.整体的研读:一卷书的图解。过去十年中,文学批判对圣经学界作出了很宝贵的贡献。在那之前,因着形式批判的影响,研究重点都放在单独的段落,不注重整体;学者将各卷书拆散,成为各自独立、互不相干的部分,然后才分析其意义。注释书因为过分强调单字的研究,使这种不平衡的趋势更加恶化,甚至字与字之间都显得没有什么关联。然而,文学批判却指出,除非从整体来看,否则各部分就没有意义。惟有先顾及整体,然后才能针对其中各部分、按着中心信息来研究。实际而言,释经的过程可以简述如下:第一,将整本书作成图表,初步分析它的思路流向;接下来,专注于每一部分,察究论证的细节;最后,再重新调整全卷的思路发展,使其与各部分息息相关。 2.文法常可提供线索,如转接性的连接词或副词;例如:「后来、所以、为此、但是、然而、同时」,和希腊文的oun,de,kai,tote,dio。 3.修辞式的问话常代表转向新的主题与段落。这类问题有时相连成串,将整个论证或一个段落往前带动。 4.时间、地点,或背景的改变,是一种常用的技巧,表示新主题与段落的出现;尤其是在故事中。 5.称谓的改变,通常特意显示:注意力已由某个团体移到另一个团体;这是最重要的技巧之一。书信式的文字中经常使用。 6.动词的时态、语气等的改变,甚至主词或受词的改变,也可能是新段落的线索。 8.偶而,一段的主题会在该段的标题语中出现。在这种特殊状况下,诠释者只需要确定:该段所有的内容都包括在作者明示的目标之内。 2.部分的研读:段落的图解。若要像解析较大的单位(一卷书)一样,来图示较小的单位(段落),垂直图比前述的水平图更好用,因为单位小。对不熟悉原文的人,我推荐使用新美国标准圣经(NASB)来进行这一类研究。这个译本虽不如其他译本流畅,可是它对直译十分讲究,因此最接近希伯来文或希腊文,让我们更清楚看出圣经作者原初的写作模式。图解的样式可以有几种(我们将用弗一5-7作实验)。许多希腊文解经课都使用复杂的图解(参图1.4),每一个词都要放在它所形容的字底下,两者的关系也要说明(参Grassmick)。费依(Gordon Fee 1983:60-76)提出句子流程解析图(图1.5),和文法分析图类似,但没有那么复杂。两者都将主词、述语,和受词放在一页的左角,而将附属词汇缩排,放在所修饰的字或片语底下。费依建议用注解来说明文法的判断,而用颜色来标示重复的字或主题。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 即使少年人变得疲乏困倦, 概念或思路之间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关联。但是要详细分类,却有困难。我的办法是把迈尔和莱斯,以及尼达等人的努力结合起来。这种分类相当重要,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研究圣经中个别的结构;对这些形式若有基本的了解,在研读不同段落的时候极为有用。所以,我将用圣经的例子来说明每一种修辞方式。 1.集合关系(collection relations,Nida:「重复」,Liefeld:「连续」)是按照要点相同的基础,将概念或事件连在一起。这是古代很常见的修辞方式。拉比称它为「串珠」,并常将弥赛亚的经文放在一起。这个方式可以说明希伯来书一章4-14节,这些串在一起的证明经文分别取自诗篇二篇7节;撒母耳记下七章17节;诗篇九十七篇7节,一O四篇4节,四十五篇6-7节,一O二篇25-27节和一一O篇1节。马太福音与五段讲论,也有类似的集合;例如,在使命讲论中的末世性段落(参太十16-22与可十三9-13)。有时,一些看似互不相干的系列,会以标示语相连。马可福音九章33-50节就是讲论奖赏与责罚的文集。这一段是围绕着「奉我的名」(37-41节)、「跌倒」(42-47节),及「盐和火」(48-50节)来组织的。 3.比较(comparison)是显示概念的相似之处或差异之处。最著名的例子是罗马书五章12-21节,亚当与基督的对比;两者都为一群人的代表(注意15节的「一人」与「众人」),或是有罪的人,或是基督徒。我们也可以举罗马书七章7-13节(过去式)与七章14-25节(现在式)两种关系的辩论为例。究竟这两段是讲未重生到重生的状况,还是过去的以色列到现在的以色列的状况(Moo 1986),我们必须作一判断。另外一个著名的对比是约翰所用的光与暗,在约翰福音一章 5节,三章 19节,尤其是八章 12-九章41节。其背景为宇宙之战,而黑暗不能「胜过」光(一5),在我们遇见基督--「世界的光」--时(八l2-13),则还有小规模的战役。箴言亦有许多智慧与愚昧相对的话,如一章7节,十五章5节等(参本书第七章有关箴言的解释)。
重复的组织法,可以用在读音或概念两方面。尼达指出,希伯来书一章1节中有五个希腊字都以p开头,而l出现了五次,还有两个副词以-os作结尾。这是一种加强记忆的方式,也使整个声明显得更有力。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八福(太五1-13)、约翰壹书写作目的之说明(约壹二12-14),以及启示录第二-三章给七个教会的信(其实是「形式上的信」)。概念的重复就更常见。在第七章中,我们会多谈希伯来诗体的对偶形式,不过在此可以先指出,散文中的对偶形式也像诗体一样常见,新约和旧约皆然。这是圣经中最常见的修辞方式。许多解经的基本错误,是强调一系列同义词中,各个名词的不同含义;例如,约翰福音二十章15-17节所用不同的「爱」字,希伯来书十章8节不同的祭,或腓立比书四章6节对祈祷的不同说法。我们总要警觉,使用不同用词或片语的原因,有可能只是文学的技巧,并没有神学的含义在内;重复或许是为了强调,我们不需要去强化各个名词之间的差异。
2.因果(cause-effect)和问题一解决(problem-solution)的关系,是先有某个动作,然后有某种结果。我们可以举无数的例子。先知对以色列的斥责,经常是采用因果方式。例如,阿摩司书二章6-16节开始为原因(「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」,6节),接下来则一一列举罪状(6下-13节),最后的结论为审判(或后果,14-16节)。阿摩司整卷书集中在社会的不公与以色列中猖獗的物质主义(如:四1斥责「巴珊的母牛……欺负贫寒的、压碎穷乏的」),以此为神审判的理由(四2,「日子快到,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上去」)。先知的弥赛亚应许,则可作为问题一解决的例子。问题是以色列公义的余民与背叛者一同受苦。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解决方法:他应许「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」(摩九8)。罪人将死亡(九10),但神自己却将「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」(11节,这意象取自住棚节)。
与此类似的是问题一回答的模式,保罗和先知都经常使用(参赛四十28-31)。在罗马书中尤其常见。保罗会提出一个修辞的问题(将他对手的看法表达出来),接着便回答这个错误的观点。这成为罗马书第三章的主要模式,开始是从犹太人的不信来看神的公平(三1-4),接着便从犹太人的不义来看神的公义(5-8节),然后谈到犹太人与外邦人都同样在罪之下(9-26节),由于需要信心,便无从夸口(27-28节),神不单是犹太人的神,也是外邦人的神(29-30节),信心能建立律法,而非废掉律法(31节)。在每个单位中,保罗都以修辞的问题开始,然后提出自己的答案。类似的问题也引介出因信称义(四l-2)、与基督联合胜过罪(六l-2)、律法与罪的问题(七 l-2、13)、神的拯救意图(八31-32),和神的公义(九 19一24,十一 l-2)等讨论。
在这个范畴内,我们也可以放入目的与结果或证明。这些都是在回答「为什么?」。目的将秩序倒转过来,说明原初的用意,而不单单只讲结果为何。这两者(目的与结果)常难以区分,不过诚如李斐德所说:「从神眷顾的角度来看,这两者的差异常并不重要」(1984:69)。无论我们翻译成「为了」(以未来为重点)或「因此」(以过去为重点),都是在强调神对全局的掌控。李斐德提到哥林多前书二章l-5节,保罗解释说,他讲道时不用高言大智,「叫(或译「因此」)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,只在乎神的大能」(亦参一29、31)。在这类例子中,目的与结果混合在一起。连接词「因为」常带进类似的神学观点证明。例如,罗马书八章29-31节说明,我们为什么可以知道「万事互相效力」(28节)。神已经预先知道他的子民,并且预定他们、呼召他们、使他们称义、得荣耀。换言之,神在掌控,所以我们能信靠他。
有些学者将交换(interchange)列为另外一段,但事实上,这只是比较的另一种变化。交换不是直接的比较,而是轮流谈论人物、事件,或类别,以制造主题的比较。约翰将彼得否认主(十八15-18、25-27)与耶稣在亚那(19-23节)和彼拉多(28-40节)面前如一的勇气穿插写来,便是最佳的例子。彼得的胆小和耶稣的勇敢成为鲜明的对比。马可也用过类似的技巧,他把一幕放在另一幕之后,产生互相解释的效果。例子有:耶稣被自己的家人(三20-21、31-35)和文士弃绝(三22-30);医治睚鲁的女儿(五21-24、35-43)当中,插入了血漏妇人的事(五25-34),两者都与洁净的律法有关;咒诅无花果树(十一12-14、20-25)刻画出洁净圣殿(十一15-19)背后的意思,就是耶路撒冷的审判。在上文所提的亚当与基督之例中(罗五12-21),也有轮流的方式。
4.描述(description)是很广的范畴,就是用进一步的资料澄清一个题目、事件,或人物。这方法也可称为连续(参Osborne和Woodward 1979:70-71),它与重复不同,因为它将讨论「延伸」,而非「复述」。这种技巧之例,如约拿书一章4-17节为他逃跑(一3)的后续描写;或亚伯拉罕所蒙的祝福(创十三14-18)在十四章l-18节有更进一步的描述。另一个例子,是基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28-32节用了两个比喻,来澄清门徒「计算代价」的重要性(26-27、33节)。那里的信息为:若不清楚结局为何,没有人敢前来作门徒。这些比喻生动地描绘出,倘若一个人想要作门徒,却不「背起他的十字架」(27节),将会如何。基督要求人与世界完全断绝关系(33节)。
总结(summation)的原则也可放在这个范畴,因为它经常是在一长段的描述之后,将全文打一个结,说明最基本的主题或结果。当然,分辨出这种技巧,对判断一段经文的基本要点很有帮助。有时这类摘要出现在一段经文的头尾,例如约书亚记十二章7、24节: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所击败的诸王如下,……共计三十一个王」。多半时候,摘要出现在最后。在历史书中,这类摘要或「接缝」,有助于题材与主题的衔接。例如,使徒行传的摘要,含括了路加最主要的神学看法,就是在教会所面对的一切危难中,神的灵都能得胜。尽管有内部的分争(六 l-6与7节)、外在的逼 -/迫(八l-九30与31节)、暴君的迫害(十二1-23与24节),及异教的问题(十九 13-19与20节),但每一项摘要的中心,都是「道」的「增长」(这个术语一方面是指福音的宣扬,一方面是指其成功的结果,就是教会的增长)。
与摘要类似的,是犹太人重提(inclusio)的技巧,就是讨论到末了,作者又回来提他最初讲的观点。这个方法将一路发展过来的基本观念覆述一遍,成为整个叙述的总结。最好的例子之一为约翰福音一章18节,那里是约翰福音序言的结论,且是一章1节主题的重复,即耶稣是神的彰显,并一直与父同在。勃朗(Raymond E.Brown)也注意到约翰的重提法,如在迦拿的神迹中,二章11节和四章46、56节;在约但河外,则有一章28节和十章40节;还有逾越节的羊羔,在一章29节及十九章36节(1966:CXXXV)。
犹太作家强调主题的另一个技巧,是交错法(chiasm),就是在连续对偶的子句或段落中,将字或事件倒转过来写。当然,旧约中经常出现这方式;以赛亚书六章10节ABC:CBA的结构便是一例(NASB):
B耳朵发沉
C眼睛昏迷
C恐怕眼睛看见
B耳朵听见
A心里明白
交错法在新约也很常见。隆德(Lund)认为,哥林多前书五章2-6节,九章 19-22节,十一章 8-12节等处,都有这现象(1942)。勃朗主张,约翰福音六章36-40节和十八章28节至十九章16节都用到交错法,他的论证颇具说服力(1966:276;1970:858-59)。
5.期待的转变(shifts in expectancy)包括许多种写作技巧。如尼达所说:「它们的重要性,就在于读者可以看出字的顺序、句法的结构,或一个字、词、句子的含义颇不寻常」(1983:36)。从某方面而言,这个范畴非常宽,可以包含修辞式问题、重复法或交错法。此外,它显然与象征用语重叠(我们将在本书第四章谈这方面)。不过,这类修辞方式超越了象征用语,是一种破格文体(anacoloutha,如尼达的说法)。然而,这类转变在结构的强调方面算是一项重点,所以必须包括在这里。耶稣的告别谈话(约十四-十六)中,有许多这类转变,因为数目太多,以致有些学者认为整段没有合一性,而是一系列重叠的传统,零乱地串在一起。结果他们提出约翰福音的「循环论」,或系列编辑说,主张这些人强将合一性加在第四卷福音书上,造成aporias,就是结构的不一致。不过,最近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发表,作者韦伯斯特(Edwin C.Webster)辩道:「这卷福音书,从文学的整体来看,结构十分严密,最基本的结构为对称的设计与平衡的单位」(1982:230)。韦伯斯特注意到,第十三至十六章中有两个同心圆式的段落,每一处都可分为三段(1982:243-45)。
一、耶稣与门徒
二、门徒与世界
1.耶稣洗他们的脚;他的榜样,十三 1-20
1.葡萄树与枝子的隐喻; 他爱的榜样,十五 1-16
2.犹大的离开 十三 21-32
2.世界的憎恨 十五 17-27
3.耶稣离开的对话 十三33-十四31
3.耶稣离开的对话,十六1-33
韦伯斯特主张,第十四章与十六章的主要部分有交错的关系,可以用来解释其中重复的主题。现代读者很难看出这种转变,可是古代人却很容易察觉和了解。如果我们明白整个结构的发展,困难便消失了。换言之,这一段并没有笨拙的不协调或重复,而是仔细设计的讲论。
高潮(climax)与关键(cruciality)也属于这个范畴。前者出现在故事中,后者则在书信中,不过两者都有相同的功能,即将作者基本论点的中枢或转捩点显示出来。医治被鬼附的孩童(可九14-29),高潮并不是神迹本身,而是那位父亲的呼喊:「我信,但我信不足,求主帮助。」这是马可作门徒主题的中枢,也成为第18-19节门徒失败的矫正,以及第29节信心祷告之必要前提。李斐德(1984:63)举了一个极佳的高潮例子,就是马太福音四章1-10节和路加福音四章1-12节中,试探不同的顺序。马太的故事,结束的高潮为世界国度的试探,这样的强调与他以弥赛亚为王的主题相配。路加则以圣殿的殿顶试探为高潮,因他的中心是圣殿,特别强调基督教来自犹太教,这是他福音书的主题之-。这两个故事的高潮,都是了解神学重点的要诀。同样,罗马书第九至十一章乃是该书的转捩点。今天大部分学者相信,这不是附加的一段,而是保罗从最前面讲到犹太人与外邦人都在罪与审判之下(一 18-三20),一路预备而来的论证。
最后,我要在此把尼达对省略(omission)的探讨(1983:33-36)也加进来。倘若某位作者刻意删去读者所期待的某一点,就造成「期待的转变」,让人惊异,也有强调作用。通常这类经文会省略特殊的字(如林前十三 4-7中的kai,或来一 5、8、10前言中的kai)。但是,偶尔会出现一种情形:原来的读者能明白为何会省略掉关键的字句,可是现代诠释者却感到非常头痛;例如,「那拦阻他的」(帖后二6-7)或「六六六」(启十三18),在解释与指认上的省略。对这两者的解释理论有上百种之多,可能我们要等到主再来,才能明白其真正的意义。
要认真研究圣经,第一步就是要衡量一段经文所处的整个情境(译注:在本书中, context译为情境、处境、上下文等)。倘若没有掌握整体的情形,就进行分析,这样开始的第一步,就注定其解释必不准确。离开情境,话语就失去意义。如果我说:「你的一切都要拿出来给它。」你一定会问:「『它』是什么意思?」「我要怎么作?」若不说明所处的状况(situation),这个命令就缺乏内容,变成毫无意义。在圣经中,上下文提供了经文所处的状况。
在研究圣经的时候,有两方面必须先行考虑:历史情境与逻辑情境。第一个范畴,就是研究该卷书导论方面的资料,以判断该书所面对的状况。第二个范畴,是用归纳法来追踪一卷书的思路发展。在仔细分析一段经文之前,这两方面都必须弄清楚。历史与逻辑情境提供了骨架,一段经文的深刻含义必须建立于其上。若骨架不强,解释的建筑必然会崩塌。
历史情境
一卷书的历史背景资料,可以从几种资源取得。最容易到手的,就是较佳注释书中的导论。许多这类注释书都有相当详细的摘要,说明各项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。最好是参考近日出版、研究深入的著作,因为最近数十年来资讯爆炸惊人。较老的著作不会提供令人兴奋的考古学发现,或近年有关圣经背景资料的新理论。旧约或新约导论也有很大的帮助,因为它们处理的范围较单卷的注释书更广。第三种资源为字典与百科全书,其中的文章不但讨论书卷,也讨论作者、主题,和背景问题。考古学与地图让我们能掌握一卷书背后的地志。像约书亚记或士师记等历史书,这方面的资料就非常重要。旧约或新约神学著作[如:赖德(Ladd)]常让我们明白单卷书的神学。最后,介绍圣经时期习俗与文化的书也很有价值,能澄清经文所特别强调之事的历史背景。
这个步骤是收集第二手资料,作为解释经文的准备(在开始解析研究的时候会用到)。从这些来源得到的资料,并不是最终的真理,却像一张蓝图,是基本的计划;当解释的建筑最后搭起来的时候,这个计画可能会更动。这些概念都是别人的,我们以后仔细研究,或许会得到不同的概念。这种预先研读有其价值,它使我们能远离二十世纪的角度,对于经文古代的情况产生更强的警觉心。在此我们需要思想几方面:
1.从某方面来说,作者的问题对历史批判研究比较重要,对用文法与历史来作解析,好像不太相关。可是,这一点仍然可以帮助我们从历史来看一卷书。举个例子,在研读小先知书的时候,我们必须知道阿摩司或撒迦利亚是在什么时候、向哪些人工作,才能明白他们话语背后的状况。了解他们的工作与背景,都会有帮助。好的导论能将一卷书的整个历史重现在眼前。这是极有价值的解释工具,因为经文乃是向原初的文化发言,若不进入那个文化,我们就无法有正确的了解。
2.写作日期也是一种解释的工具,使读者能解开经文的含义。如果但以理书是在马加比时期写的,它的意思便截然不同。倘若提摩太前书是在第一世纪下半叶,由保罗的一位门徒所写,它的色调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雅各书是写给西元一一O年之后分散的团体〔如:狄比流(Dibelius)的理论〕,它的解释也会不同。对这三个问题,我都持传统立场,这立场与我对经文的解释密切相关。启示录的时间,放在尼禄作王时(Nero,西元60年上下),和多米田作王时(Domitian,西元90年上下),在象征的解释上会有很大的区别。
3.经文的对象,在文意上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他们的境遇决定了该卷书的内容。当然,这个问题在新约更重要,因为旧约的作品总是写给以色列人的。然而,先知书背后的状况(例如以赛亚时代全国的情形)深深影响这些书卷信息的了解。希伯来书究竟是写给犹太人,还是外邦人,或是混合的教会,在解释上的确有区别。事实上,最后一类人的可能性最大,不过信中谈到的是有关犹太人的问题。几年以前,福音神学社收到一份彼得前书的论文,作者假定该书信是写给一间犹太人的教会。有人问他,如果收信者中有犹太人,也有外邦人,对他的论文会有什么影响;他必须承认,这一点会改变他整个论文。而事实上,彼得前书的对象的确是混合的会众。
4.在这四方面中,目的和主题对解释最有帮助。在研读任何一段经文的时候,我们对于该卷书面对的问题和环境,都要有基本的知识,也要知道作者是用什么主题来谈这些问题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约翰在第一封书信中,是面对诺斯底派刍形的挑战,就很可能误解约翰壹书一章8-10节护教的语气。直到最近,注释家才开始研讨个别书卷的圣经神学。可是这是极有用的解释工具。倘若注意到一卷书的整体观点,对于其中个别声明的解释,就更容易准确。如果明白路加的重点是救恩(历史),同时他也强调一些主题,诸如圣灵、敬拜,和社会关怀,对了解其中的比喻--如财主与拉撒路(路十六)--会有很大的帮助。
从这些来源所得到的资料,可以作为一种过滤器,将个别经文在其中滤过。在详细的解析与研读经文之后,这些预备资料或许会需要修正。它的目的是将解释的定律规范得更窄一些,让我们所提的问题更恰当,强迫我们回到原初作者的文化,以及经文背后当初的状况中。这样,我们就不至于将二十世纪的意义读入第一世纪的用语中。这种方法让人事先进行了解,将经文与背景衔接起来。同时,这些资料必须摆在经文面前,不要放在它背后;也就是说,在我们仔细研读个别段落时,或许会需要修正它。这份材料绝不可以勉强经文跟随它的指引,因为它是次要的,而主要的知识必须经由研读经文本身而来。
逻辑情境
实际来说,逻辑情境是解释最基本的要素。我告诉班上的学生,如果有人打瞌睡,没有听到我问的问题,而倘若他/她回答「情境」,可能有一半答对的机会。这个词本身对经文的影响是一系列的。最佳的图解方式,就是一连串的同心圆,以经文为中心,向外扩展(参图1.1)。
愈靠近中心,对经文意义的影响力愈大。例如,辨认文学形式的风格,可以帮助诠释者认出何为比喻,可是这一点比不上其他经文对该段经文的影响力。比方说,我们可以辨识出启示录是启示文学;虽然两约之间与希腊式的启示文学都可以提供重要的类似处,但是启示录大部分象征乃是取自旧约。从另一端来看,一个词汇或观念的意义,最后的仲裁者为其直接的上下文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中用的词,与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中的用法,不保证一定相同。因为语言的运作本来就不是如此;每一个字都有许多含义,作者的用法要视当时的上下文而定,与前一段中的用法无干。aphiemi一字是很好的例子,在约翰福音十四章27节为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」,而十六章28节则为「我又离开世界」。这两者不能互相解释,因为它们的用法正好相反。在第一处,耶稣给门徒一样东西;在第二处,他则是将一样东西(他自己!)从他们当中拿走。而「赦免」一字,我们更不能按平常的用法来理解(如:约壹一9)。其他经文能帮助我们了解语意学的范围(这个字可能有的不同含义),但是惟有当时的上下文足以限定可能性,指出其实际的意义。
图1.l也将以下几章包括在内。一般所谓的「归纳法查经」包含几个层面,就是将整卷书作图表,和分析一个段落。归纳法一般是指个人对一段经文专心的研究,不使用其他工具书(如注释书)或资料。我直接进入经文,对它的含义自己下结论,而不是借用别人的结论来了解。这种掌握批判力的方法,使我在必须用注释书和其他材料进一步深入研究经文时,不致过分受到它们的影响。我必须先有定见,再与其他人的结论互动。否则的话,我只是复述别人的意见而已。现成的资料带我进入经文背后的状况,而我自己归纳式的研读,使我能预备好资料,来评估各种注释书。
阿德勒(Adler)和范道伦(Van Doren)合写的名著《如何阅读一本书》(How to Read a Book,1972:16-20),探究阅读的四个阶段:(1)初步阅读,重点在辨认其中的用词和文句;(2)调查式阅读,就是综览全书,找出基本的架构和主要思想;(3)分析式阅读,对全书作深入的研究,尽可能彻底明白其信息;(4)同类式阅读,即将所得的信息与其他类似书籍作比较,对主题作出第一手的详细分析。前面两个阶段是归纳法,后面两个则是以研究为取向,不单用到原来的文字(原著),也用到次要文字(对该书的解释,或其他人所写相关的书)。
本章要探讨调查式阅读法。阿德勒和范道伦将这个方法分为两个途径(1972:32-44)。第一,翻阅介绍部分(序言、目录、索引),并浏览主要的篇章与段落,以明白全书基本的进展与中心思想。就圣经的一卷书而言,这就包括前言与各段的标题(如果用研读本圣经),再加上熟读重要的几章(如:罗-、三、六、九、十二)。第二,速读全书,不要停下来思想个别的段落或难明的观念。这方式使我们可以明白并记住全书的要点,不致立刻迷失在一些细节中。
我要将这种调查式阅读法的范围再扩展一些,把结构发展也包括在内;我称之为「书卷图解法」(Osborne and Woodward 1979:29-32)。这时候最好用一本分段良好的圣经。我们必须记住,章节并没有被默示。事实上,是直到一五五一年圣经才分成节,有一位巴黎的出版商,名叫司提番那(Stephanus),他用了六个月将全本圣经分成节,然后出版了他最新的希腊文版。根据传说,司提番那是骑在马背上作这件事,而他分节的依据,是马行进时对他笔的震动!后来司提番那的版本普及各处,没有人敢擅自更动,而他的分法一直沿用到如今。问题是,司提番那对章节的分法常有问题,可是一般人以为他的判断乃是正确的,以致在解释各章各节时,没有顾到上下文。所以,我们在决定意义时,绝不可倚赖节的区分。分段乃是了解各卷书思路发展的要诀。
我教导教会团体查经法,时常发现,对初学者而言,最困难的事就是速读每一段,写下重点。大家很容易一头栽进细节,却不懂得鸟瞰全章。在这一步,我们需要从整体来看,学生应当学习用六到八个字来作每一段的摘要。如果我们读得太细,摘要就会只反映出全段的前几节,而不是整段。这种错误会使整个研究有所偏差。在图1.2和1.3中,我用约拿书和腓立比书作例子,以说明这种方法在旧约和新约中都可使用。
如约拿书的图解所示,按照顺序,以简短的话囊括每一段,只要顺着摘要看,就可以感受到全卷的思路。而综览整个图解,全书的轮廓便一清二楚。例如,我们很容易看出,第三章成就了第一章原初的目的,就是到尼尼微的使命,以及百姓的悔改。因此,全卷有两处平行,第一与第三章,第二与第四章。再者,重点为后一个平行,因此约拿书的要义不在于宣教,而在于约拿(和以色列)对神的态度,和对神要怜悯之人的态度。第四章是「故事的精髓」,教导神的怜悯。
第一章
第二章
第三章
第四章
1-3 传道的命令;违逆与逃避
1-5 祈祷;约拿的痛 苦
1-3上 二度命令;约拿顺服
1-4 约拿发怒;神发问
4-12 神的风暴;水手的惧怕
6-9 祈祷;约拿的信心
3下-9 传道与尼尼微 的悔改
5-8 神的教导(1):蓖 麻枯萎,约拿发怒
13-16 水手顺服,抛 约拿入海17 大鱼吞约拿入腹
10 被吞出
10 神的赦免
9-11 神的教导(2):神的怜悯
第一章
第二章
第三章
第四章
1-2 问安
1-4 合一与谦卑,不自夸
1-4 警告犹太派
1 站稳
3-8 感恩:为相交与分享
5-11基督谦卑与高升的榜样
4下-6 保罗辉煌的资历
2-3 祈求合一
9-11 祈祷:为他们的爱心和分辨力
12-13 责任与神赐的 能力
7-11 为基督看一切为 有损
4-7 劝勉:喜乐、温柔、为挂虑祈祷
12-14 他的囚禁使福音广传
14-18 作见证,不埋怨、不相争
12-14 竭力更多得着基督
8-9 思想美事并且去行
15-18 因敌人播扬福音而欢喜
19-24 称赞提摩太真正的关心
15-16 听从的呼吁
10-13 喜乐与满员,因他们的分享与基督的预备
18下-26无论得释或殉道都将欢喜
25-30 称赞以巴弗提不顾性命
17-21 真假教师的对 比
14-19 喜乐与满足进一步的解释
27-30 虽遇逼 -/迫仍然同心合意
20-23 颂荣与最后问安
如果我们将第四章定为「约拿的忿怒」或「忿怒得回答」,就会错失了要点,即:约拿学到了神赦免的意义。所以,每一段标题都必须抓住该段的要义。不过,我们也必须记得,这只是预备性的综览,在仔细分解之后,若有需要变更之处,还要修改。像约拿书或腓立比书的长度,作综览大约需花四十到四十五分钟。
现在让我们更深一层,一步步探索如何制作图解。
一、速读段落最有效的方式,是拿一枝笔。一面读,一面写下摘要。这样作最能专心。速读一段经文(或稍为仔细去读),最大的问题是心思不集中。我常发现,读完一段之后,我的心却在想当时面对的问题,或当天要作的事,结果必须重读一遍(有时几遍!)。如果我边读边记,强调第一印象,就比较能专心。还有,如果以一句话作摘要嫌不足,我就抓住那段思路的进展(如,腓四4-7一连串的劝勉;见图解)。这时,速读并写笔记的方法便有助益。这步骤的价值为:所作的图解成了地图,可以追踪整卷书的走向。以后再仔细研读各个段落时,我可以一眼就断定某句声明前后的思路。
二、在图解全卷之后,就可以回头检查,寻找全书各段中思路进展的模式。如果发现段落之间思路中断,就应当用单线作记号(参上图)。内容类似的段落组成全书的大段,这样便能看得更准确。有些思路的改变很容易看出,如从保罗对自己的评语(一12-26)转为论腓立比的情形(一27-28),或进一步从腓立比人的情形转而称赞提摩太和以巴弗提(二19-30)。有些改变则不太容易察觉,如从谦卑的提醒(二1-11)稍微转向警告(二12-18),或将四章1节与三章17-21节相连,而不与四章2-9节相连。至于最后一点,读者暂时只能猜测原因,等到仔细解析全书之后,才能完全澄清。
这就是我为何将约拿书和腓立比书都放在这里的原因。约拿书是圣经中大纲与章的分段符合的少数几卷之一,可以成为简单的范例。约拿书中惟一的问题,是一章17节究竟是第一章的结论,还是第二章的引言。腓立比书就复杂得多,需要更仔细的思想。它是教导式的题材,不是故事或叙述(如约拿书)。这类文字的分段常较突兀(如二25-30,三l-6),全书的进展也不容易确定。不过,这两个例子的作法,都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整卷书的思想进展。
另外一个困难,是找出模式改变的方法。虽然圣经每一段的组织都有意义,但思想模式却常不容易辨识。司陶特(D.Stuart)说:「模式的分辨,在于寻找一些主要的特点,诸如发展、继续、独特的片语形式、中心或枢纽的字、平行、交错、含括等重复或进展的模式。模式的要诀常是重复与进展」(1980:36;强调字为原书所有)。华德·凯瑟( W.Kaiser)提供了更详细的说明,列出八个发掘思想单位「缝合处」的「线索」(1981:7l-72):
1.重复的名词、片语、子句,或句子,可以成为标题语,引介各个部 分,或成为末尾的结语,结束每个段落。
7.钥字、命题,或概念的重复,暗示出一个段落的范围。
在我们速读各段、写摘要时,这些基本的模式中断方式颇有帮助。既知道这些可能性,在制作图表的时候,就可以判断思路的转折。甚至在作更详细的解析时,这些中断方式也有用处。
三、最后一步,是再将各段区分成大单位,以双线来表示。教导类的书卷,如腓立比书,这样做格外有价值。这个过程与前一步差不多,可是思想的单位比段落更大,乃是建造在第二步之上。作完这个步骤,把结果与我们所收集的注释书和导论比较一下,颇有帮助。我们甚至可以将结果记在图上[例如,将注释者的名字,如Ralph Martin(丁道尔系列的腓立比书注释)或Gerald Hawthorne(Word系列的腓立比书注释),放在他们所认为该分大单位的所在〕,以作比较,在未来的研究上可以指引我们的思想。不过,最重要的是,一开始我们要自己作归纳研究,未完成之前,千万不要去查阅第二手资料。否则我们一定会被其他人的看法控制。归纳法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关卡,使我们不致盲目随从注释书,可以找出自己的解释,不致像鹦鹉学舌一般,只是重复某些专家学者的意见。
然而,这个方法对诗篇与箴言并不适用(个别的诗篇或许可以使用,但是整卷却无法采用)。虽然许多人尝试将诗篇用不同的方法分类,但是以主题来架构的模式太过肤浅。箴言也相仿;直线型发展的部分(如第一-九章,或三十一章)可以用图解,但是箴言的收集部分,却无法从整体的角度来研究(参本书第七、八章)。
再者,或许有人会问,这个方式对很长的书卷(如以赛亚书或耶利米书)是否适用?这个问题问得有理。虽然长书卷的图解比较难,但是我衷心相信,这样作很有帮助。容我用一卷书作例子。这卷书不算最长,但却是圣经中最困难的部分之一,那就是启示录。我不作整个图表(请读者自行尝试),而是讨论其结构的暗示(第二、三步)。我们在经文里面寻找模式时,可以看出启示录的组织是天与地之间循环出现。只要浏览图解,就会看到第一、四-五、七(十)、十四-十五,和十九章l-10节是天上的情景,而第二-三、六、八-九、十一-十三,和十六-十八章是发生在地上的事。结论部分(十九11-二十二2)则将天与地结合起来。此外,在这个轮转的模式中,天上的景象主要是赞美与敬拜,而地上的景象则是愈来愈混乱、痛苦,神的审判也愈发加重。这个模式最佳的证明,是印、角,和碗的关系。用归纳法的表,我们可以看出,它们的组织模式是相同的。因此,印、角,和碗乃是以循环来组织,特色是审判与毁灭的逐渐加强(受影响的程度,六8为地的四分之一,七7-8为三分之一,十六3-4为全地)。天上与地上景象的对比,指出全书具合一的主题,即神的主权(垂直方向),并导致水平方面,就是要求教会信靠神,无论目前与未来的苦难为何。
我要再度强调,这只是初步的大纲,还不是最后的。它代表读者的观点,但不一定是原作者的看法(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)。迈尔(Meyer)和莱斯(Rice)(1982:155-92)举例说明,读者的角度会如何影响一段文字的组织图,不过他们承认,「读者的任务……是建立自己对该段文字架构的了解,并使这架构尽量接近作者的原意」(p.156)。他们的实验小组研读一段有关铁路的文章,来显示个人的角度如何影响对文章结构的看法。当然,因为每个人的期待不同,对经文架构的分析就很不一样。我们必须承认,自己的前提很容易影响对经文的看法。在归纳法的过程中,读者扮演关键性的角色,而若要明了作者原初的设计,就必须更进一步研究。然而在解释的过程中,归纳法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,因为它能够提供观点。



我喜欢较简单的方块式图解(图l.6),过于字或片语的图解(图1.4和1.5),因为它可以表达子句的层面,较能呈现全面性。另外两个方式将每个字或片语都作图示,而方块图解只图示主要与次要的子句(或长片语)。这三种图,在层次上一个比一个广--字、片语、子句;而子句则是一段话的大块结构。方块法有一些缺失;例如,它不像另外两个图那样能表达细节。然而,它有三项优点,足能盖过其缺点:(1)它比较简单,花的时间较少;忙碌的牧师或平信徒能够持续使用;(2)在子句结构中,大部分其他关系(诸如形容词、名词的修饰语、副词,或修饰动词的介系词片语)也能显示出来;(3)句子图解的目的,是将一段经文的思路以一目了然的方式表达出来,而不是要深究文法的细节。另外两种方式,对于目视太过复杂,无法达到这一点。在解析研究中(第二至五章),文法的细节会显露出来,可是在这样的初步阶段,讲究细节不但无助,反而有损。文法最好留到以后的过程再考究。此外,在下面的解析过程,图解就不那么重要,因为是要澄清句子当中的细节,而不是要目视思想的流程。所以,句子图解已经足以达到我们的目标,不需要详细的文法图解。
在句子图解中,首先要作的,是区别主要子句与次要子句。我们的教育体制很少讲到这方面,实在让人讶异。在希腊文课上,我常问学生,他们最后一次上文法课或句子解析课是什么时候,大部分人从初中之后就再没有接触;有几位主修英语的学生,在大学里面也完全没有碰过!因此,我们不得不承认,我们对这方面的知识非常缺乏。
子句乃是句子中含有主词与述词的部分,例如,「我看见那个男孩」(主要子句)或「因为我看见那个男孩」(附属或次要子句)。以上两句的分别为:第一句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句子,而第二句却不能。在第一次读圣经的句子时,我觉得最好的办法,是向自己大声念出每一个子句,看看哪一句为不整全的句子,哪一句可以独立。
例如,腓立比书二章6节(参以下图解)。我还是喜欢用直译式的译本,如新美国标准圣经,因为它比较接近希腊文和希伯来文,在研经上有好处(当然,懂得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的人,可以直接用原文圣经)。腓立比书二章6节的经文为:「那位(Who),虽然他曾以神的形像存在,(却)不以与神同等为一件要抓紧的事。」这里的「那位」引进二章6-11节的道成肉身伟大赞美诗,因此当视为名词(第5节的「基督耶稣」)。我们开口读这一节,就会发现,「虽然他曾以神的形像存在」,本身并不能独立为一句话,所以它是主要子句(「他……不以与神同等为一件要抓紧的事」)的附属子句。作图解时,我们将次要子句缩入半寸左右,并用箭头指出它要修饰的子句。
虽然他曾以神的形像存在
那位……不以与神同等为一件要抓紧的事。
许多人喜欢将修饰子句缩排在所形容之字的下面。这方法在视觉上效果不错,可是我感到它颇难使用。许多附属子句是修饰一个子句的最后一个字,用这个方法会占用很多空间。此外,保罗很会用回旋式句子,例如,以弗所书一章3-14节就是一句话,其中的结构复杂得不得了。用这种方式图解,一张纸绝对不够,需要用八尺宽的纸!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是缩入半寸,并将箭头放在要修饰的子句底下。
在方块图解中,有几方面需要注意(图1.7)。第一,箭头要指向所修饰的词,而附属子句或片语比要修饰的子句缩进半英寸。第二,缩排子句经常会一连串,因为会有次要子句修饰另一个次要子句的情形。这就是句子图解的主要价值所在,因为它可以使这种复杂的关系一目了然,增进我们对思路进展的了解。第三,平行子句或片语要以箭头(如果它们是附属的,如以上弗一5-6的两个介系词片语)或直线(如果它们不是附属的,如第7节的两个名词)相连。以弗所书一5-7有四个连续的附属关系。倘若我们以横接的方式来写,需要很多空间;而用箭头,就简单又有效。箭头也使我们能顺着经文的顺序,避免搞混。次要子句若在前面,箭头就朝下(参以下腓二6的图解),若在后面,箭头就朝上(如以上弗一5-7)。
在圣经中辨认子句最有效的方式,也许是研究连接的字。对圣经研究而言,这一点尤其真确,因为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经常使用连接词。我们必须问,它是否为对等连接词(以及、但是、可是、既…又…、不但…而且…、不是…就是…、因此、因为、于是)--衔接平行句或主要的子句,还是附属连接词(除非、之前、之后、同时、当时、自从、因为、即、如果、虽然、虽、以致、为要、除外、如同、那么、那里)--衔接修饰子句。
我们也可以陈明附属的关系,就是用一些记号来代表各种语法关系(如,T代表时间[temporal],Ca代表原因[causl],Cn代表让步[concessive],Cd代表条件[conditional],R代表结果[result],Rel代表相关[relative],P代表目的[Purpose],Me代表媒介[means], Ma代表方式[manner], I代表工具[instrumental])。这些记号可以写在箭头旁边,如此,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段经文中附属子句的模式。我要以腓立比书二章6-11节整首道成肉身的赞美诗来作图解示范(参图1.7)。
这个图使人一眼看出,主要的两段是耶稣的行动和神的行动。在前者之下有三个基本概念:耶稣的顺服、倒空和谦卑。在后者之下只有一个主要概念--神升高的行动--以及两个次要概念--万膝都要跪拜和万口都要承认。我们会立刻注意到,这可以成为初略的讲道大纲。事实上,方块图解可以成为讲章或查经的初步纲要。在查看图中的子句模式时,也可以马上看出哪些是主要子句,哪些是次要子句(正如我们在腓二6-11所见)。
不过,在此要提出两项警告:第一,大纲就像图解一样,乃是初步的,仔细解析经文之后,可能需要更改。第二,句法的关系固然对判断思想的主要部分很有帮助,可是却不能自动作出判断。子句常有平行现象(如7-8节的倒空与谦卑,或10-11节的跪拜与承认),必须结合成为一个要点。还有一件事也很要紧,有时在作者的实际思想发展中,文法上的附属语和主要子句同样重要,甚至比它更重要。保罗在这方面最出名。如果附属概念有详尽的说明,就是一个记号,表示作者认为它是要点。例如,腓立比书二章2节说:「要有同一个心思、同一份爱、在灵里合-、心思朝向同一个目标,使我的喜乐满足」。显然,这里最要强调的并不是使保罗的喜乐满足,而是腓立比

教会的和谐;连续四个附属子句说明了带给保罗更大喜乐的途径。在讲道大纲中,要点应当是和谐,而不是喜乐。同样,在腓立比书的赞美诗中,保罗用了两个附属子句来修饰倒空(7节)和谦卑(8节)显示保罗实际上是在强调道成肉身的事(「成为人的样式」)。
传道人应当从直线图发展出讲道大纲。最佳的方法,是将它与图并排,对照重点。在这个步骤中,讲道大纲就像查经材料一样。可是我在十五章中会提出,在一篇解经讲道中,经文应当主导其架构。如果我们主控经文,勉强它来配合自己预先想好的信息,就不是在传讲神的话,而是在分享我们的想法。当然,有时候这类信息(专题式)有其必要,不过它不算真正的解经讲道。所以,大纲必须配合经文的架构:
一、谦卑的光景(二6-8)
1.心思的光景(6节)
1)他的本体
2)他的决定
2.存在的光景(7-8节)
l)他的道成肉身(7节)
a.他的本体
b.他的形像
2)他的谦卑(8节)
a.他的样式
b.他的顺服
二、高举的光景(二9-11)
1.被神高举(9节)
l)他的新地位
2)他伟大的名
2.被人和万物高举(10-11节)
1)藉服从来高举(10节)
2)藉承认来高举(11节)
a. 宇宙性
b.内容
c.结果
这仍然只是初步的大纲,要等到解析全部完成后,才能定案。到那时候,经文可以转变成满有动力的讲道模型(参本书第十六章;Liefeld 1984:115-20)。不过到目前为止,我们对腓立比书二章6-11节的研读非常有意义,不但作出了未来查经或讲道的大纲,也提供了可能的信息。除了本段之外,只有约翰福音一章 l-18节对道成肉身和基督的高举有如此深刻的神学反思。在前半段中(6-8节),三个主要子句都提到道成肉身的时刻。第一处是从负面来讲,耶稣拒绝神性的特权与荣耀(6节);接下来是从正面来谈倒空与谦卑,耶稣将他的人性(「奴仆的形像」,7节,与8节相较)加在他的神性(「神的形像」,6节)上。这种仆人基督论,成为基督徒行为的模范或准则(注意5节),高举的段落(9-11节)因此更显得动人。我们若像基督一样「谦卑自己」(与3节比较),神就必将我们高举,分享基督的荣耀。当然,我们并没有「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」。但是,约翰福音十七章22节的平行句,在此颇有帮助: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,我已赐给他们」。若分享耶稣的谦卑,就将分享他的高举。
我要再用一段旧约经文来说明这个方法。请看以赛亚书四十章27-31节。首先,我们需要明白这段圣经背景的大环境。第四十章是以赛亚书第二大段(四十-五十五章)的开始,其中心为「仆人之歌」,与神对列国普遍救赎的爱。这开头的一章是一首奇妙的赞美诗,颂扬神的全能与救赎的爱。后半段(18-31节)为一连串修辞式的问题,责备以色列缺乏信心。神无可比拟(18-20节)、无限伟大,远超地上或天上的一切荣耀(21-26节),他会为他的子民行事(27-31节)。
你为何说,哦,雅各
并肯定,哦,以色列,
我的道路向上主隐藏
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?
你不知道吗?
你未曾听过吗?
永在的神,上主,地极的创造者
并不疲乏或困倦。
他赐力量给疲乏的,
又将力量加给赐缺乏能力的。
强壮的年轻人全然跌倒,
但那等候上主的将得着新的力量:
他们将如鹰展翅上腾,
他们将奔跑而不困倦,
他们将行走而不疲乏。
我们首先会注意到,旧约经文缺乏附属子句。由于希伯来文不太使用连接词,图解的帮助便不像新约那么大。类似这样的诗体经文,大半都是主要子句。在散文中,主要的连接词(即「以及」)子句占多数。所以,我们必须寻求修辞的模式,并注意思想有否改变。在这时候,直线式的图解仍有帮助,因为他将句子并排在一起。这一段中,我们立刻注意到,思想是以对句出现。每一个概念都重复强调。并且,在引介的问题之后,有一种ABA的模式。第一组对句是以神为中心,讲到神是怎样的一位(28节下),他怎样赐予有需要的人(29节)。中间的对句(30节)将神的子民与强壮的战士作对比,这些人也会力量衰竭;最后一组对句(31节)说明等候上主的结果。初步的研究大纲可能如下:
前言——神义论的问题(27-28节上)
一、神会行动( 28下-29节)
1.他是怎样的一位(28节下)
2.他会做什么事(29节)
二、接受他的能力(30-31节)
1.没有接受的人(30节)
2.接受的人(31节)
另外一种可能,是将第30节作为第二大点,第31节作第三大点。当我们研究思想模式时,有一件事立刻会让我们吃惊:这三段都是采用运动或军事的意象,尤其是奔跑与困倦的衔接。神绝不会困倦,年轻的运动员却会;凡信靠神的人会得着他的力量,得着奇妙的坚忍力量。这样的一段经文显然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。3.弧形法。富乐(Dan Fuller)发展出一种新方法来图解一个段落(或一卷书),他称之为「弧形法」(他在富勒神学院教释经学的讲义第四章,未出版)。这方法的前提与方块图解相同,但是他以水平的方式写,而不用垂直的方式,从许多方面看,他对视觉的效果更好,更容易捕捉思想的发展(参图1.8)。相关的子句以弧形相连,并注明其关系,然后整个单位再加上弧形,并注明关系。从这种图,我们很容易察觉一个整体中的重点与次要之点,也能够准确指出各部分的关系。
每个人最好能发展出自己的关系表与钥字;不过,除了前面的表(参上文)之外,我还要提出一些连接子句的缩写方式:Adv代表反义词[adversative]、Pr代表进展[progression]、S代表系列[series]、Co代表比较[comparison]、Wh-Pts代表整体一部分[whole-Parts]、Id—Int 代表概念-解释[ide—ainterpretation]、QS-AS代表问题-答案[question-answer]。至于附属关系,用Inf代表推理[inference]、Loc代表地点[locative,“in”]、 G代表根基或基础[ground]。这些记号的价值,是一眼就能看出思想的发展。我个人建议,保罗(以及新约几位作者)比较繁复的句子,用方块式图解,这是垂直模式中视觉较佳的方式;而旧约的平行子句最好用弧形法,因为方块图解的价值不大。
事实上,若将弧形法用在保罗书信,以弗所书一章5-7节就可以显出一个问题。第5节很不容易用弧形来表达,因为三个介系词子片语都修饰主要的子句,而不是互相修饰。用弧形法,看来会像它们在彼此修饰,但其实它们只修饰主要子句。不过,这种视觉模式仍十分有用。
作一段经文的思路结构图解时,常会碰到修辞学的技巧,也就是传达信息的文学方法。这便是概念的第三种情境,也是它的最后一个层面;这三个层面分别为:全卷书组织模式的宏观层面、分段的中间层面,与各段之内的写作技巧。以下四章所要探讨的题目,就是这种微观的层面(经文用字的详细结构)。
我们可以参照亚里斯多德(Aristotle)对修辞学的古典定义:「它是讲究如何以最佳方式说服人接受某个思想的艺术」(Kessler1982:2)。修辞学的研究,常与形式(文体)和功能(组织技巧)混为一谈。修辞学最古典的四种分类为西塞罗(Cicero)所定,即:虚构、编排、体裁,与记忆的技巧。风格并不在这些范围之下,因为按定义而言,「修辞批判」(rhetorical Criticism)主要是在谈沟通的技巧,换言之,就是谈作者表达论点的技巧与组织模式。克斯乐(Kessler 1982:13-14)主张,在修辞的分析中,最重要的乃是与历史无关的一面--亦即,与经文本身相关的一面。在本段中,我采用这个观点来看经文的结构,并探究圣经作者(及其他人)用什么文学技巧来串联他们的论点(其他类型的修辞批判,参第四章的附注)。
重复的组织法,可以用在读音或概念两方面。尼达指出,希伯来书一章1节中有五个希腊字都以p开头,而l出现了五次,还有两个副词以-os作结尾。这是一种加强记忆的方式,也使整个声明显得更有力。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八福(太五1-13)、约翰壹书写作目的之说明(约壹二12-14),以及启示录第二-三章给七个教会的信(其实是「形式上的信」)。概念的重复就更常见。在第七章中,我们会多谈希伯来诗体的对偶形式,不过在此可以先指出,散文中的对偶形式也像诗体一样常见,新约和旧约皆然。这是圣经中最常见的修辞方式。许多解经的基本错误,是强调一系列同义词中,各个名词的不同含义;例如,约翰福音二十章15-17节所用不同的「爱」字,希伯来书十章8节不同的祭,或腓立比书四章6节对祈祷的不同说法。我们总要警觉,使用不同用词或片语的原因,有可能只是文学的技巧,并没有神学的含义在内;重复或许是为了强调,我们不需要去强化各个名词之间的差异。
2.因果(cause-effect)和问题一解决(problem-solution)的关系,是先有某个动作,然后有某种结果。我们可以举无数的例子。先知对以色列的斥责,经常是采用因果方式。例如,阿摩司书二章6-16节开始为原因(「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」,6节),接下来则一一列举罪状(6下-13节),最后的结论为审判(或后果,14-16节)。阿摩司整卷书集中在社会的不公与以色列中猖獗的物质主义(如:四1斥责「巴珊的母牛……欺负贫寒的、压碎穷乏的」),以此为神审判的理由(四2,「日子快到,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上去」)。先知的弥赛亚应许,则可作为问题一解决的例子。问题是以色列公义的余民与背叛者一同受苦。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解决方法:他应许「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」(摩九8)。罪人将死亡(九10),但神自己却将「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」(11节,这意象取自住棚节)。
与此类似的是问题一回答的模式,保罗和先知都经常使用(参赛四十28-31)。在罗马书中尤其常见。保罗会提出一个修辞的问题(将他对手的看法表达出来),接着便回答这个错误的观点。这成为罗马书第三章的主要模式,开始是从犹太人的不信来看神的公平(三1-4),接着便从犹太人的不义来看神的公义(5-8节),然后谈到犹太人与外邦人都同样在罪之下(9-26节),由于需要信心,便无从夸口(27-28节),神不单是犹太人的神,也是外邦人的神(29-30节),信心能建立律法,而非废掉律法(31节)。在每个单位中,保罗都以修辞的问题开始,然后提出自己的答案。类似的问题也引介出因信称义(四l-2)、与基督联合胜过罪(六l-2)、律法与罪的问题(七 l-2、13)、神的拯救意图(八31-32),和神的公义(九 19一24,十一 l-2)等讨论。
在这个范畴内,我们也可以放入目的与结果或证明。这些都是在回答「为什么?」。目的将秩序倒转过来,说明原初的用意,而不单单只讲结果为何。这两者(目的与结果)常难以区分,不过诚如李斐德所说:「从神眷顾的角度来看,这两者的差异常并不重要」(1984:69)。无论我们翻译成「为了」(以未来为重点)或「因此」(以过去为重点),都是在强调神对全局的掌控。李斐德提到哥林多前书二章l-5节,保罗解释说,他讲道时不用高言大智,「叫(或译「因此」)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,只在乎神的大能」(亦参一29、31)。在这类例子中,目的与结果混合在一起。连接词「因为」常带进类似的神学观点证明。例如,罗马书八章29-31节说明,我们为什么可以知道「万事互相效力」(28节)。神已经预先知道他的子民,并且预定他们、呼召他们、使他们称义、得荣耀。换言之,神在掌控,所以我们能信靠他。 A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
B耳朵发沉
C眼睛昏迷
C恐怕眼睛看见
B耳朵听见
A心里明白
交错法在新约也很常见。隆德(Lund)认为,哥林多前书五章2-6节,九章 19-22节,十一章 8-12节等处,都有这现象(1942)。勃朗主张,约翰福音六章36-40节和十八章28节至十九章16节都用到交错法,他的论证颇具说服力(1966:276;1970:858-59)。
5.期待的转变(shifts in expectancy)包括许多种写作技巧。如尼达所说:「它们的重要性,就在于读者可以看出字的顺序、句法的结构,或一个字、词、句子的含义颇不寻常」(1983:36)。从某方面而言,这个范畴非常宽,可以包含修辞式问题、重复法或交错法。此外,它显然与象征用语重叠(我们将在本书第四章谈这方面)。不过,这类修辞方式超越了象征用语,是一种破格文体(anacoloutha,如尼达的说法)。然而,这类转变在结构的强调方面算是一项重点,所以必须包括在这里。耶稣的告别谈话(约十四-十六)中,有许多这类转变,因为数目太多,以致有些学者认为整段没有合一性,而是一系列重叠的传统,零乱地串在一起。结果他们提出约翰福音的「循环论」,或系列编辑说,主张这些人强将合一性加在第四卷福音书上,造成aporias,就是结构的不一致。不过,最近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发表,作者韦伯斯特(Edwin C.Webster)辩道:「这卷福音书,从文学的整体来看,结构十分严密,最基本的结构为对称的设计与平衡的单位」(1982:230)。韦伯斯特注意到,第十三至十六章中有两个同心圆式的段落,每一处都可分为三段(1982:243-45)。
有些学者将交换(interchange)列为另外一段,但事实上,这只是比较的另一种变化。交换不是直接的比较,而是轮流谈论人物、事件,或类别,以制造主题的比较。约翰将彼得否认主(十八15-18、25-27)与耶稣在亚那(19-23节)和彼拉多(28-40节)面前如一的勇气穿插写来,便是最佳的例子。彼得的胆小和耶稣的勇敢成为鲜明的对比。马可也用过类似的技巧,他把一幕放在另一幕之后,产生互相解释的效果。例子有:耶稣被自己的家人(三20-21、31-35)和文士弃绝(三22-30);医治睚鲁的女儿(五21-24、35-43)当中,插入了血漏妇人的事(五25-34),两者都与洁净的律法有关;咒诅无花果树(十一12-14、20-25)刻画出洁净圣殿(十一15-19)背后的意思,就是耶路撒冷的审判。在上文所提的亚当与基督之例中(罗五12-21),也有轮流的方式。
4.描述(description)是很广的范畴,就是用进一步的资料澄清一个题目、事件,或人物。这方法也可称为连续(参Osborne和Woodward 1979:70-71),它与重复不同,因为它将讨论「延伸」,而非「复述」。这种技巧之例,如约拿书一章4-17节为他逃跑(一3)的后续描写;或亚伯拉罕所蒙的祝福(创十三14-18)在十四章l-18节有更进一步的描述。另一个例子,是基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28-32节用了两个比喻,来澄清门徒「计算代价」的重要性(26-27、33节)。那里的信息为:若不清楚结局为何,没有人敢前来作门徒。这些比喻生动地描绘出,倘若一个人想要作门徒,却不「背起他的十字架」(27节),将会如何。基督要求人与世界完全断绝关系(33节)。
总结(summation)的原则也可放在这个范畴,因为它经常是在一长段的描述之后,将全文打一个结,说明最基本的主题或结果。当然,分辨出这种技巧,对判断一段经文的基本要点很有帮助。有时这类摘要出现在一段经文的头尾,例如约书亚记十二章7、24节: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所击败的诸王如下,……共计三十一个王」。多半时候,摘要出现在最后。在历史书中,这类摘要或「接缝」,有助于题材与主题的衔接。例如,使徒行传的摘要,含括了路加最主要的神学看法,就是在教会所面对的一切危难中,神的灵都能得胜。尽管有内部的分争(六 l-6与7节)、外在的逼 -/迫(八l-九30与31节)、暴君的迫害(十二1-23与24节),及异教的问题(十九 13-19与20节),但每一项摘要的中心,都是「道」的「增长」(这个术语一方面是指福音的宣扬,一方面是指其成功的结果,就是教会的增长)。
与摘要类似的,是犹太人重提(inclusio)的技巧,就是讨论到末了,作者又回来提他最初讲的观点。这个方法将一路发展过来的基本观念覆述一遍,成为整个叙述的总结。最好的例子之一为约翰福音一章18节,那里是约翰福音序言的结论,且是一章1节主题的重复,即耶稣是神的彰显,并一直与父同在。勃朗(Raymond E.Brown)也注意到约翰的重提法,如在迦拿的神迹中,二章11节和四章46、56节;在约但河外,则有一章28节和十章40节;还有逾越节的羊羔,在一章29节及十九章36节(1966:CXXXV)。
犹太作家强调主题的另一个技巧,是交错法(chiasm),就是在连续对偶的子句或段落中,将字或事件倒转过来写。当然,旧约中经常出现这方式;以赛亚书六章10节ABC:CBA的结构便是一例(NASB):
一、耶稣与门徒
二、门徒与世界
1.耶稣洗他们的脚;他的榜样,十三 1-20
1.葡萄树与枝子的隐喻; 他爱的榜样,十五 1-16
2.犹大的离开 十三 21-32
2.世界的憎恨 十五 17-27
3.耶稣离开的对话 十三33-十四31
3.耶稣离开的对话,十六1-33
韦伯斯特主张,第十四章与十六章的主要部分有交错的关系,可以用来解释其中重复的主题。现代读者很难看出这种转变,可是古代人却很容易察觉和了解。如果我们明白整个结构的发展,困难便消失了。换言之,这一段并没有笨拙的不协调或重复,而是仔细设计的讲论。
高潮(climax)与关键(cruciality)也属于这个范畴。前者出现在故事中,后者则在书信中,不过两者都有相同的功能,即将作者基本论点的中枢或转捩点显示出来。医治被鬼附的孩童(可九14-29),高潮并不是神迹本身,而是那位父亲的呼喊:「我信,但我信不足,求主帮助。」这是马可作门徒主题的中枢,也成为第18-19节门徒失败的矫正,以及第29节信心祷告之必要前提。李斐德(1984:63)举了一个极佳的高潮例子,就是马太福音四章1-10节和路加福音四章1-12节中,试探不同的顺序。马太的故事,结束的高潮为世界国度的试探,这样的强调与他以弥赛亚为王的主题相配。路加则以圣殿的殿顶试探为高潮,因他的中心是圣殿,特别强调基督教来自犹太教,这是他福音书的主题之-。这两个故事的高潮,都是了解神学重点的要诀。同样,罗马书第九至十一章乃是该书的转捩点。今天大部分学者相信,这不是附加的一段,而是保罗从最前面讲到犹太人与外邦人都在罪与审判之下(一 18-三20),一路预备而来的论证。
最后,我要在此把尼达对省略(omission)的探讨(1983:33-36)也加进来。倘若某位作者刻意删去读者所期待的某一点,就造成「期待的转变」,让人惊异,也有强调作用。通常这类经文会省略特殊的字(如林前十三 4-7中的kai,或来一 5、8、10前言中的kai)。但是,偶尔会出现一种情形:原来的读者能明白为何会省略掉关键的字句,可是现代诠释者却感到非常头痛;例如,「那拦阻他的」(帖后二6-7)或「六六六」(启十三18),在解释与指认上的省略。对这两者的解释理论有上百种之多,可能我们要等到主再来,才能明白其真正的意义。
要认真研究圣经,第一步就是要衡量一段经文所处的整个情境(译注:在本书中, context译为情境、处境、上下文等)。倘若没有掌握整体的情形,就进行分析,这样开始的第一步,就注定其解释必不准确。离开情境,话语就失去意义。如果我说:「你的一切都要拿出来给它。」你一定会问:「『它』是什么意思?」「我要怎么作?」若不说明所处的状况(situation),这个命令就缺乏内容,变成毫无意义。在圣经中,上下文提供了经文所处的状况。
在研究圣经的时候,有两方面必须先行考虑:历史情境与逻辑情境。第一个范畴,就是研究该卷书导论方面的资料,以判断该书所面对的状况。第二个范畴,是用归纳法来追踪一卷书的思路发展。在仔细分析一段经文之前,这两方面都必须弄清楚。历史与逻辑情境提供了骨架,一段经文的深刻含义必须建立于其上。若骨架不强,解释的建筑必然会崩塌。
历史情境
一卷书的历史背景资料,可以从几种资源取得。最容易到手的,就是较佳注释书中的导论。许多这类注释书都有相当详细的摘要,说明各项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。最好是参考近日出版、研究深入的著作,因为最近数十年来资讯爆炸惊人。较老的著作不会提供令人兴奋的考古学发现,或近年有关圣经背景资料的新理论。旧约或新约导论也有很大的帮助,因为它们处理的范围较单卷的注释书更广。第三种资源为字典与百科全书,其中的文章不但讨论书卷,也讨论作者、主题,和背景问题。考古学与地图让我们能掌握一卷书背后的地志。像约书亚记或士师记等历史书,这方面的资料就非常重要。旧约或新约神学著作[如:赖德(Ladd)]常让我们明白单卷书的神学。最后,介绍圣经时期习俗与文化的书也很有价值,能澄清经文所特别强调之事的历史背景。
这个步骤是收集第二手资料,作为解释经文的准备(在开始解析研究的时候会用到)。从这些来源得到的资料,并不是最终的真理,却像一张蓝图,是基本的计划;当解释的建筑最后搭起来的时候,这个计画可能会更动。这些概念都是别人的,我们以后仔细研究,或许会得到不同的概念。这种预先研读有其价值,它使我们能远离二十世纪的角度,对于经文古代的情况产生更强的警觉心。在此我们需要思想几方面:
1.从某方面来说,作者的问题对历史批判研究比较重要,对用文法与历史来作解析,好像不太相关。可是,这一点仍然可以帮助我们从历史来看一卷书。举个例子,在研读小先知书的时候,我们必须知道阿摩司或撒迦利亚是在什么时候、向哪些人工作,才能明白他们话语背后的状况。了解他们的工作与背景,都会有帮助。好的导论能将一卷书的整个历史重现在眼前。这是极有价值的解释工具,因为经文乃是向原初的文化发言,若不进入那个文化,我们就无法有正确的了解。
2.写作日期也是一种解释的工具,使读者能解开经文的含义。如果但以理书是在马加比时期写的,它的意思便截然不同。倘若提摩太前书是在第一世纪下半叶,由保罗的一位门徒所写,它的色调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雅各书是写给西元一一O年之后分散的团体〔如:狄比流(Dibelius)的理论〕,它的解释也会不同。对这三个问题,我都持传统立场,这立场与我对经文的解释密切相关。启示录的时间,放在尼禄作王时(Nero,西元60年上下),和多米田作王时(Domitian,西元90年上下),在象征的解释上会有很大的区别。
3.经文的对象,在文意上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他们的境遇决定了该卷书的内容。当然,这个问题在新约更重要,因为旧约的作品总是写给以色列人的。然而,先知书背后的状况(例如以赛亚时代全国的情形)深深影响这些书卷信息的了解。希伯来书究竟是写给犹太人,还是外邦人,或是混合的教会,在解释上的确有区别。事实上,最后一类人的可能性最大,不过信中谈到的是有关犹太人的问题。几年以前,福音神学社收到一份彼得前书的论文,作者假定该书信是写给一间犹太人的教会。有人问他,如果收信者中有犹太人,也有外邦人,对他的论文会有什么影响;他必须承认,这一点会改变他整个论文。而事实上,彼得前书的对象的确是混合的会众。
4.在这四方面中,目的和主题对解释最有帮助。在研读任何一段经文的时候,我们对于该卷书面对的问题和环境,都要有基本的知识,也要知道作者是用什么主题来谈这些问题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约翰在第一封书信中,是面对诺斯底派刍形的挑战,就很可能误解约翰壹书一章8-10节护教的语气。直到最近,注释家才开始研讨个别书卷的圣经神学。可是这是极有用的解释工具。倘若注意到一卷书的整体观点,对于其中个别声明的解释,就更容易准确。如果明白路加的重点是救恩(历史),同时他也强调一些主题,诸如圣灵、敬拜,和社会关怀,对了解其中的比喻--如财主与拉撒路(路十六)--会有很大的帮助。
从这些来源所得到的资料,可以作为一种过滤器,将个别经文在其中滤过。在详细的解析与研读经文之后,这些预备资料或许会需要修正。它的目的是将解释的定律规范得更窄一些,让我们所提的问题更恰当,强迫我们回到原初作者的文化,以及经文背后当初的状况中。这样,我们就不至于将二十世纪的意义读入第一世纪的用语中。这种方法让人事先进行了解,将经文与背景衔接起来。同时,这些资料必须摆在经文面前,不要放在它背后;也就是说,在我们仔细研读个别段落时,或许会需要修正它。这份材料绝不可以勉强经文跟随它的指引,因为它是次要的,而主要的知识必须经由研读经文本身而来。
逻辑情境
实际来说,逻辑情境是解释最基本的要素。我告诉班上的学生,如果有人打瞌睡,没有听到我问的问题,而倘若他/她回答「情境」,可能有一半答对的机会。这个词本身对经文的影响是一系列的。最佳的图解方式,就是一连串的同心圆,以经文为中心,向外扩展(参图1.1)。
愈靠近中心,对经文意义的影响力愈大。例如,辨认文学形式的风格,可以帮助诠释者认出何为比喻,可是这一点比不上其他经文对该段经文的影响力。比方说,我们可以辨识出启示录是启示文学;虽然两约之间与希腊式的启示文学都可以提供重要的类似处,但是启示录大部分象征乃是取自旧约。从另一端来看,一个词汇或观念的意义,最后的仲裁者为其直接的上下文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中用的词,与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中的用法,不保证一定相同。因为语言的运作本来就不是如此;每一个字都有许多含义,作者的用法要视当时的上下文而定,与前一段中的用法无干。aphiemi一字是很好的例子,在约翰福音十四章27节为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」,而十六章28节则为「我又离开世界」。这两者不能互相解释,因为它们的用法正好相反。在第一处,耶稣给门徒一样东西;在第二处,他则是将一样东西(他自己!)从他们当中拿走。而「赦免」一字,我们更不能按平常的用法来理解(如:约壹一9)。其他经文能帮助我们了解语意学的范围(这个字可能有的不同含义),但是惟有当时的上下文足以限定可能性,指出其实际的意义。
图1.l也将以下几章包括在内。一般所谓的「归纳法查经」包含几个层面,就是将整卷书作图表,和分析一个段落。归纳法一般是指个人对一段经文专心的研究,不使用其他工具书(如注释书)或资料。我直接进入经文,对它的含义自己下结论,而不是借用别人的结论来了解。这种掌握批判力的方法,使我在必须用注释书和其他材料进一步深入研究经文时,不致过分受到它们的影响。我必须先有定见,再与其他人的结论互动。否则的话,我只是复述别人的意见而已。现成的资料带我进入经文背后的状况,而我自己归纳式的研读,使我能预备好资料,来评估各种注释书。
阿德勒(Adler)和范道伦(Van Doren)合写的名著《如何阅读一本书》(How to Read a Book,1972:16-20),探究阅读的四个阶段:(1)初步阅读,重点在辨认其中的用词和文句;(2)调查式阅读,就是综览全书,找出基本的架构和主要思想;(3)分析式阅读,对全书作深入的研究,尽可能彻底明白其信息;(4)同类式阅读,即将所得的信息与其他类似书籍作比较,对主题作出第一手的详细分析。前面两个阶段是归纳法,后面两个则是以研究为取向,不单用到原来的文字(原著),也用到次要文字(对该书的解释,或其他人所写相关的书)。
本章要探讨调查式阅读法。阿德勒和范道伦将这个方法分为两个途径(1972:32-44)。第一,翻阅介绍部分(序言、目录、索引),并浏览主要的篇章与段落,以明白全书基本的进展与中心思想。就圣经的一卷书而言,这就包括前言与各段的标题(如果用研读本圣经),再加上熟读重要的几章(如:罗-、三、六、九、十二)。第二,速读全书,不要停下来思想个别的段落或难明的观念。这方式使我们可以明白并记住全书的要点,不致立刻迷失在一些细节中。
我要将这种调查式阅读法的范围再扩展一些,把结构发展也包括在内;我称之为「书卷图解法」(Osborne and Woodward 1979:29-32)。这时候最好用一本分段良好的圣经。我们必须记住,章节并没有被默示。事实上,是直到一五五一年圣经才分成节,有一位巴黎的出版商,名叫司提番那(Stephanus),他用了六个月将全本圣经分成节,然后出版了他最新的希腊文版。根据传说,司提番那是骑在马背上作这件事,而他分节的依据,是马行进时对他笔的震动!后来司提番那的版本普及各处,没有人敢擅自更动,而他的分法一直沿用到如今。问题是,司提番那对章节的分法常有问题,可是一般人以为他的判断乃是正确的,以致在解释各章各节时,没有顾到上下文。所以,我们在决定意义时,绝不可倚赖节的区分。分段乃是了解各卷书思路发展的要诀。
我教导教会团体查经法,时常发现,对初学者而言,最困难的事就是速读每一段,写下重点。大家很容易一头栽进细节,却不懂得鸟瞰全章。在这一步,我们需要从整体来看,学生应当学习用六到八个字来作每一段的摘要。如果我们读得太细,摘要就会只反映出全段的前几节,而不是整段。这种错误会使整个研究有所偏差。在图1.2和1.3中,我用约拿书和腓立比书作例子,以说明这种方法在旧约和新约中都可使用。
如约拿书的图解所示,按照顺序,以简短的话囊括每一段,只要顺着摘要看,就可以感受到全卷的思路。而综览整个图解,全书的轮廓便一清二楚。例如,我们很容易看出,第三章成就了第一章原初的目的,就是到尼尼微的使命,以及百姓的悔改。因此,全卷有两处平行,第一与第三章,第二与第四章。再者,重点为后一个平行,因此约拿书的要义不在于宣教,而在于约拿(和以色列)对神的态度,和对神要怜悯之人的态度。第四章是「故事的精髓」,教导神的怜悯。
第一章
第二章
第三章
第四章
1-3 传道的命令;违逆与逃避
1-5 祈祷;约拿的痛 苦
1-3上 二度命令;约拿顺服
1-4 约拿发怒;神发问
4-12 神的风暴;水手的惧怕
6-9 祈祷;约拿的信心
3下-9 传道与尼尼微 的悔改
5-8 神的教导(1):蓖 麻枯萎,约拿发怒
13-16 水手顺服,抛 约拿入海17 大鱼吞约拿入腹
10 被吞出
10 神的赦免
9-11 神的教导(2):神的怜悯
第一章
第二章
第三章
第四章
1-2 问安
1-4 合一与谦卑,不自夸
1-4 警告犹太派
1 站稳
3-8 感恩:为相交与分享
5-11基督谦卑与高升的榜样
4下-6 保罗辉煌的资历
2-3 祈求合一
9-11 祈祷:为他们的爱心和分辨力
12-13 责任与神赐的 能力
7-11 为基督看一切为 有损
4-7 劝勉:喜乐、温柔、为挂虑祈祷
12-14 他的囚禁使福音广传
14-18 作见证,不埋怨、不相争
12-14 竭力更多得着基督
8-9 思想美事并且去行
15-18 因敌人播扬福音而欢喜
19-24 称赞提摩太真正的关心
15-16 听从的呼吁
10-13 喜乐与满员,因他们的分享与基督的预备
18下-26无论得释或殉道都将欢喜
25-30 称赞以巴弗提不顾性命
17-21 真假教师的对 比
14-19 喜乐与满足进一步的解释
27-30 虽遇逼 -/迫仍然同心合意
20-23 颂荣与最后问安
如果我们将第四章定为「约拿的忿怒」或「忿怒得回答」,就会错失了要点,即:约拿学到了神赦免的意义。所以,每一段标题都必须抓住该段的要义。不过,我们也必须记得,这只是预备性的综览,在仔细分解之后,若有需要变更之处,还要修改。像约拿书或腓立比书的长度,作综览大约需花四十到四十五分钟。
现在让我们更深一层,一步步探索如何制作图解。
一、速读段落最有效的方式,是拿一枝笔。一面读,一面写下摘要。这样作最能专心。速读一段经文(或稍为仔细去读),最大的问题是心思不集中。我常发现,读完一段之后,我的心却在想当时面对的问题,或当天要作的事,结果必须重读一遍(有时几遍!)。如果我边读边记,强调第一印象,就比较能专心。还有,如果以一句话作摘要嫌不足,我就抓住那段思路的进展(如,腓四4-7一连串的劝勉;见图解)。这时,速读并写笔记的方法便有助益。这步骤的价值为:所作的图解成了地图,可以追踪整卷书的走向。以后再仔细研读各个段落时,我可以一眼就断定某句声明前后的思路。
二、在图解全卷之后,就可以回头检查,寻找全书各段中思路进展的模式。如果发现段落之间思路中断,就应当用单线作记号(参上图)。内容类似的段落组成全书的大段,这样便能看得更准确。有些思路的改变很容易看出,如从保罗对自己的评语(一12-26)转为论腓立比的情形(一27-28),或进一步从腓立比人的情形转而称赞提摩太和以巴弗提(二19-30)。有些改变则不太容易察觉,如从谦卑的提醒(二1-11)稍微转向警告(二12-18),或将四章1节与三章17-21节相连,而不与四章2-9节相连。至于最后一点,读者暂时只能猜测原因,等到仔细解析全书之后,才能完全澄清。
这就是我为何将约拿书和腓立比书都放在这里的原因。约拿书是圣经中大纲与章的分段符合的少数几卷之一,可以成为简单的范例。约拿书中惟一的问题,是一章17节究竟是第一章的结论,还是第二章的引言。腓立比书就复杂得多,需要更仔细的思想。它是教导式的题材,不是故事或叙述(如约拿书)。这类文字的分段常较突兀(如二25-30,三l-6),全书的进展也不容易确定。不过,这两个例子的作法,都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整卷书的思想进展。
另外一个困难,是找出模式改变的方法。虽然圣经每一段的组织都有意义,但思想模式却常不容易辨识。司陶特(D.Stuart)说:「模式的分辨,在于寻找一些主要的特点,诸如发展、继续、独特的片语形式、中心或枢纽的字、平行、交错、含括等重复或进展的模式。模式的要诀常是重复与进展」(1980:36;强调字为原书所有)。华德·凯瑟( W.Kaiser)提供了更详细的说明,列出八个发掘思想单位「缝合处」的「线索」(1981:7l-72):
1.重复的名词、片语、子句,或句子,可以成为标题语,引介各个部 分,或成为末尾的结语,结束每个段落。
7.钥字、命题,或概念的重复,暗示出一个段落的范围。
在我们速读各段、写摘要时,这些基本的模式中断方式颇有帮助。既知道这些可能性,在制作图表的时候,就可以判断思路的转折。甚至在作更详细的解析时,这些中断方式也有用处。
三、最后一步,是再将各段区分成大单位,以双线来表示。教导类的书卷,如腓立比书,这样做格外有价值。这个过程与前一步差不多,可是思想的单位比段落更大,乃是建造在第二步之上。作完这个步骤,把结果与我们所收集的注释书和导论比较一下,颇有帮助。我们甚至可以将结果记在图上[例如,将注释者的名字,如Ralph Martin(丁道尔系列的腓立比书注释)或Gerald Hawthorne(Word系列的腓立比书注释),放在他们所认为该分大单位的所在〕,以作比较,在未来的研究上可以指引我们的思想。不过,最重要的是,一开始我们要自己作归纳研究,未完成之前,千万不要去查阅第二手资料。否则我们一定会被其他人的看法控制。归纳法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关卡,使我们不致盲目随从注释书,可以找出自己的解释,不致像鹦鹉学舌一般,只是重复某些专家学者的意见。
然而,这个方法对诗篇与箴言并不适用(个别的诗篇或许可以使用,但是整卷却无法采用)。虽然许多人尝试将诗篇用不同的方法分类,但是以主题来架构的模式太过肤浅。箴言也相仿;直线型发展的部分(如第一-九章,或三十一章)可以用图解,但是箴言的收集部分,却无法从整体的角度来研究(参本书第七、八章)。
再者,或许有人会问,这个方式对很长的书卷(如以赛亚书或耶利米书)是否适用?这个问题问得有理。虽然长书卷的图解比较难,但是我衷心相信,这样作很有帮助。容我用一卷书作例子。这卷书不算最长,但却是圣经中最困难的部分之一,那就是启示录。我不作整个图表(请读者自行尝试),而是讨论其结构的暗示(第二、三步)。我们在经文里面寻找模式时,可以看出启示录的组织是天与地之间循环出现。只要浏览图解,就会看到第一、四-五、七(十)、十四-十五,和十九章l-10节是天上的情景,而第二-三、六、八-九、十一-十三,和十六-十八章是发生在地上的事。结论部分(十九11-二十二2)则将天与地结合起来。此外,在这个轮转的模式中,天上的景象主要是赞美与敬拜,而地上的景象则是愈来愈混乱、痛苦,神的审判也愈发加重。这个模式最佳的证明,是印、角,和碗的关系。用归纳法的表,我们可以看出,它们的组织模式是相同的。因此,印、角,和碗乃是以循环来组织,特色是审判与毁灭的逐渐加强(受影响的程度,六8为地的四分之一,七7-8为三分之一,十六3-4为全地)。天上与地上景象的对比,指出全书具合一的主题,即神的主权(垂直方向),并导致水平方面,就是要求教会信靠神,无论目前与未来的苦难为何。
我要再度强调,这只是初步的大纲,还不是最后的。它代表读者的观点,但不一定是原作者的看法(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)。迈尔(Meyer)和莱斯(Rice)(1982:155-92)举例说明,读者的角度会如何影响一段文字的组织图,不过他们承认,「读者的任务……是建立自己对该段文字架构的了解,并使这架构尽量接近作者的原意」(p.156)。他们的实验小组研读一段有关铁路的文章,来显示个人的角度如何影响对文章结构的看法。当然,因为每个人的期待不同,对经文架构的分析就很不一样。我们必须承认,自己的前提很容易影响对经文的看法。在归纳法的过程中,读者扮演关键性的角色,而若要明了作者原初的设计,就必须更进一步研究。然而在解释的过程中,归纳法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,因为它能够提供观点。



我喜欢较简单的方块式图解(图l.6),过于字或片语的图解(图1.4和1.5),因为它可以表达子句的层面,较能呈现全面性。另外两个方式将每个字或片语都作图示,而方块图解只图示主要与次要的子句(或长片语)。这三种图,在层次上一个比一个广--字、片语、子句;而子句则是一段话的大块结构。方块法有一些缺失;例如,它不像另外两个图那样能表达细节。然而,它有三项优点,足能盖过其缺点:(1)它比较简单,花的时间较少;忙碌的牧师或平信徒能够持续使用;(2)在子句结构中,大部分其他关系(诸如形容词、名词的修饰语、副词,或修饰动词的介系词片语)也能显示出来;(3)句子图解的目的,是将一段经文的思路以一目了然的方式表达出来,而不是要深究文法的细节。另外两种方式,对于目视太过复杂,无法达到这一点。在解析研究中(第二至五章),文法的细节会显露出来,可是在这样的初步阶段,讲究细节不但无助,反而有损。文法最好留到以后的过程再考究。此外,在下面的解析过程,图解就不那么重要,因为是要澄清句子当中的细节,而不是要目视思想的流程。所以,句子图解已经足以达到我们的目标,不需要详细的文法图解。
在句子图解中,首先要作的,是区别主要子句与次要子句。我们的教育体制很少讲到这方面,实在让人讶异。在希腊文课上,我常问学生,他们最后一次上文法课或句子解析课是什么时候,大部分人从初中之后就再没有接触;有几位主修英语的学生,在大学里面也完全没有碰过!因此,我们不得不承认,我们对这方面的知识非常缺乏。
子句乃是句子中含有主词与述词的部分,例如,「我看见那个男孩」(主要子句)或「因为我看见那个男孩」(附属或次要子句)。以上两句的分别为:第一句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句子,而第二句却不能。在第一次读圣经的句子时,我觉得最好的办法,是向自己大声念出每一个子句,看看哪一句为不整全的句子,哪一句可以独立。
例如,腓立比书二章6节(参以下图解)。我还是喜欢用直译式的译本,如新美国标准圣经,因为它比较接近希腊文和希伯来文,在研经上有好处(当然,懂得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的人,可以直接用原文圣经)。腓立比书二章6节的经文为:「那位(Who),虽然他曾以神的形像存在,(却)不以与神同等为一件要抓紧的事。」这里的「那位」引进二章6-11节的道成肉身伟大赞美诗,因此当视为名词(第5节的「基督耶稣」)。我们开口读这一节,就会发现,「虽然他曾以神的形像存在」,本身并不能独立为一句话,所以它是主要子句(「他……不以与神同等为一件要抓紧的事」)的附属子句。作图解时,我们将次要子句缩入半寸左右,并用箭头指出它要修饰的子句。
虽然他曾以神的形像存在
那位……不以与神同等为一件要抓紧的事。
许多人喜欢将修饰子句缩排在所形容之字的下面。这方法在视觉上效果不错,可是我感到它颇难使用。许多附属子句是修饰一个子句的最后一个字,用这个方法会占用很多空间。此外,保罗很会用回旋式句子,例如,以弗所书一章3-14节就是一句话,其中的结构复杂得不得了。用这种方式图解,一张纸绝对不够,需要用八尺宽的纸!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是缩入半寸,并将箭头放在要修饰的子句底下。
在方块图解中,有几方面需要注意(图1.7)。第一,箭头要指向所修饰的词,而附属子句或片语比要修饰的子句缩进半英寸。第二,缩排子句经常会一连串,因为会有次要子句修饰另一个次要子句的情形。这就是句子图解的主要价值所在,因为它可以使这种复杂的关系一目了然,增进我们对思路进展的了解。第三,平行子句或片语要以箭头(如果它们是附属的,如以上弗一5-6的两个介系词片语)或直线(如果它们不是附属的,如第7节的两个名词)相连。以弗所书一5-7有四个连续的附属关系。倘若我们以横接的方式来写,需要很多空间;而用箭头,就简单又有效。箭头也使我们能顺着经文的顺序,避免搞混。次要子句若在前面,箭头就朝下(参以下腓二6的图解),若在后面,箭头就朝上(如以上弗一5-7)。
在圣经中辨认子句最有效的方式,也许是研究连接的字。对圣经研究而言,这一点尤其真确,因为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经常使用连接词。我们必须问,它是否为对等连接词(以及、但是、可是、既…又…、不但…而且…、不是…就是…、因此、因为、于是)--衔接平行句或主要的子句,还是附属连接词(除非、之前、之后、同时、当时、自从、因为、即、如果、虽然、虽、以致、为要、除外、如同、那么、那里)--衔接修饰子句。
我们也可以陈明附属的关系,就是用一些记号来代表各种语法关系(如,T代表时间[temporal],Ca代表原因[causl],Cn代表让步[concessive],Cd代表条件[conditional],R代表结果[result],Rel代表相关[relative],P代表目的[Purpose],Me代表媒介[means], Ma代表方式[manner], I代表工具[instrumental])。这些记号可以写在箭头旁边,如此,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段经文中附属子句的模式。我要以腓立比书二章6-11节整首道成肉身的赞美诗来作图解示范(参图1.7)。
这个图使人一眼看出,主要的两段是耶稣的行动和神的行动。在前者之下有三个基本概念:耶稣的顺服、倒空和谦卑。在后者之下只有一个主要概念--神升高的行动--以及两个次要概念--万膝都要跪拜和万口都要承认。我们会立刻注意到,这可以成为初略的讲道大纲。事实上,方块图解可以成为讲章或查经的初步纲要。在查看图中的子句模式时,也可以马上看出哪些是主要子句,哪些是次要子句(正如我们在腓二6-11所见)。
不过,在此要提出两项警告:第一,大纲就像图解一样,乃是初步的,仔细解析经文之后,可能需要更改。第二,句法的关系固然对判断思想的主要部分很有帮助,可是却不能自动作出判断。子句常有平行现象(如7-8节的倒空与谦卑,或10-11节的跪拜与承认),必须结合成为一个要点。还有一件事也很要紧,有时在作者的实际思想发展中,文法上的附属语和主要子句同样重要,甚至比它更重要。保罗在这方面最出名。如果附属概念有详尽的说明,就是一个记号,表示作者认为它是要点。例如,腓立比书二章2节说:「要有同一个心思、同一份爱、在灵里合-、心思朝向同一个目标,使我的喜乐满足」。显然,这里最要强调的并不是使保罗的喜乐满足,而是腓立比

教会的和谐;连续四个附属子句说明了带给保罗更大喜乐的途径。在讲道大纲中,要点应当是和谐,而不是喜乐。同样,在腓立比书的赞美诗中,保罗用了两个附属子句来修饰倒空(7节)和谦卑(8节)显示保罗实际上是在强调道成肉身的事(「成为人的样式」)。
传道人应当从直线图发展出讲道大纲。最佳的方法,是将它与图并排,对照重点。在这个步骤中,讲道大纲就像查经材料一样。可是我在十五章中会提出,在一篇解经讲道中,经文应当主导其架构。如果我们主控经文,勉强它来配合自己预先想好的信息,就不是在传讲神的话,而是在分享我们的想法。当然,有时候这类信息(专题式)有其必要,不过它不算真正的解经讲道。所以,大纲必须配合经文的架构:
一、谦卑的光景(二6-8)
1.心思的光景(6节)
1)他的本体
2)他的决定
2.存在的光景(7-8节)
l)他的道成肉身(7节)
a.他的本体
b.他的形像
2)他的谦卑(8节)
a.他的样式
b.他的顺服
二、高举的光景(二9-11)
1.被神高举(9节)
l)他的新地位
2)他伟大的名
2.被人和万物高举(10-11节)
1)藉服从来高举(10节)
2)藉承认来高举(11节)
a. 宇宙性
b.内容
c.结果
这仍然只是初步的大纲,要等到解析全部完成后,才能定案。到那时候,经文可以转变成满有动力的讲道模型(参本书第十六章;Liefeld 1984:115-20)。不过到目前为止,我们对腓立比书二章6-11节的研读非常有意义,不但作出了未来查经或讲道的大纲,也提供了可能的信息。除了本段之外,只有约翰福音一章 l-18节对道成肉身和基督的高举有如此深刻的神学反思。在前半段中(6-8节),三个主要子句都提到道成肉身的时刻。第一处是从负面来讲,耶稣拒绝神性的特权与荣耀(6节);接下来是从正面来谈倒空与谦卑,耶稣将他的人性(「奴仆的形像」,7节,与8节相较)加在他的神性(「神的形像」,6节)上。这种仆人基督论,成为基督徒行为的模范或准则(注意5节),高举的段落(9-11节)因此更显得动人。我们若像基督一样「谦卑自己」(与3节比较),神就必将我们高举,分享基督的荣耀。当然,我们并没有「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」。但是,约翰福音十七章22节的平行句,在此颇有帮助: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,我已赐给他们」。若分享耶稣的谦卑,就将分享他的高举。
我要再用一段旧约经文来说明这个方法。请看以赛亚书四十章27-31节。首先,我们需要明白这段圣经背景的大环境。第四十章是以赛亚书第二大段(四十-五十五章)的开始,其中心为「仆人之歌」,与神对列国普遍救赎的爱。这开头的一章是一首奇妙的赞美诗,颂扬神的全能与救赎的爱。后半段(18-31节)为一连串修辞式的问题,责备以色列缺乏信心。神无可比拟(18-20节)、无限伟大,远超地上或天上的一切荣耀(21-26节),他会为他的子民行事(27-31节)。
你为何说,哦,雅各
并肯定,哦,以色列,
我的道路向上主隐藏
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?
你不知道吗?
你未曾听过吗?
永在的神,上主,地极的创造者
并不疲乏或困倦。
他赐力量给疲乏的,
又将力量加给赐缺乏能力的。
强壮的年轻人全然跌倒,
但那等候上主的将得着新的力量:
他们将如鹰展翅上腾,
他们将奔跑而不困倦,
他们将行走而不疲乏。
我们首先会注意到,旧约经文缺乏附属子句。由于希伯来文不太使用连接词,图解的帮助便不像新约那么大。类似这样的诗体经文,大半都是主要子句。在散文中,主要的连接词(即「以及」)子句占多数。所以,我们必须寻求修辞的模式,并注意思想有否改变。在这时候,直线式的图解仍有帮助,因为他将句子并排在一起。这一段中,我们立刻注意到,思想是以对句出现。每一个概念都重复强调。并且,在引介的问题之后,有一种ABA的模式。第一组对句是以神为中心,讲到神是怎样的一位(28节下),他怎样赐予有需要的人(29节)。中间的对句(30节)将神的子民与强壮的战士作对比,这些人也会力量衰竭;最后一组对句(31节)说明等候上主的结果。初步的研究大纲可能如下:
前言——神义论的问题(27-28节上)
一、神会行动( 28下-29节)
1.他是怎样的一位(28节下)
2.他会做什么事(29节)
二、接受他的能力(30-31节)
1.没有接受的人(30节)
2.接受的人(31节)
另外一种可能,是将第30节作为第二大点,第31节作第三大点。当我们研究思想模式时,有一件事立刻会让我们吃惊:这三段都是采用运动或军事的意象,尤其是奔跑与困倦的衔接。神绝不会困倦,年轻的运动员却会;凡信靠神的人会得着他的力量,得着奇妙的坚忍力量。这样的一段经文显然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。3.弧形法。富乐(Dan Fuller)发展出一种新方法来图解一个段落(或一卷书),他称之为「弧形法」(他在富勒神学院教释经学的讲义第四章,未出版)。这方法的前提与方块图解相同,但是他以水平的方式写,而不用垂直的方式,从许多方面看,他对视觉的效果更好,更容易捕捉思想的发展(参图1.8)。相关的子句以弧形相连,并注明其关系,然后整个单位再加上弧形,并注明关系。从这种图,我们很容易察觉一个整体中的重点与次要之点,也能够准确指出各部分的关系。
每个人最好能发展出自己的关系表与钥字;不过,除了前面的表(参上文)之外,我还要提出一些连接子句的缩写方式:Adv代表反义词[adversative]、Pr代表进展[progression]、S代表系列[series]、Co代表比较[comparison]、Wh-Pts代表整体一部分[whole-Parts]、Id—Int 代表概念-解释[ide—ainterpretation]、QS-AS代表问题-答案[question-answer]。至于附属关系,用Inf代表推理[inference]、Loc代表地点[locative,“in”]、 G代表根基或基础[ground]。这些记号的价值,是一眼就能看出思想的发展。我个人建议,保罗(以及新约几位作者)比较繁复的句子,用方块式图解,这是垂直模式中视觉较佳的方式;而旧约的平行子句最好用弧形法,因为方块图解的价值不大。
事实上,若将弧形法用在保罗书信,以弗所书一章5-7节就可以显出一个问题。第5节很不容易用弧形来表达,因为三个介系词子片语都修饰主要的子句,而不是互相修饰。用弧形法,看来会像它们在彼此修饰,但其实它们只修饰主要子句。不过,这种视觉模式仍十分有用。
作一段经文的思路结构图解时,常会碰到修辞学的技巧,也就是传达信息的文学方法。这便是概念的第三种情境,也是它的最后一个层面;这三个层面分别为:全卷书组织模式的宏观层面、分段的中间层面,与各段之内的写作技巧。以下四章所要探讨的题目,就是这种微观的层面(经文用字的详细结构)。
我们可以参照亚里斯多德(Aristotle)对修辞学的古典定义:「它是讲究如何以最佳方式说服人接受某个思想的艺术」(Kessler1982:2)。修辞学的研究,常与形式(文体)和功能(组织技巧)混为一谈。修辞学最古典的四种分类为西塞罗(Cicero)所定,即:虚构、编排、体裁,与记忆的技巧。风格并不在这些范围之下,因为按定义而言,「修辞批判」(rhetorical Criticism)主要是在谈沟通的技巧,换言之,就是谈作者表达论点的技巧与组织模式。克斯乐(Kessler 1982:13-14)主张,在修辞的分析中,最重要的乃是与历史无关的一面--亦即,与经文本身相关的一面。在本段中,我采用这个观点来看经文的结构,并探究圣经作者(及其他人)用什么文学技巧来串联他们的论点(其他类型的修辞批判,参第四章的附注)。
重复的组织法,可以用在读音或概念两方面。尼达指出,希伯来书一章1节中有五个希腊字都以p开头,而l出现了五次,还有两个副词以-os作结尾。这是一种加强记忆的方式,也使整个声明显得更有力。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八福(太五1-13)、约翰壹书写作目的之说明(约壹二12-14),以及启示录第二-三章给七个教会的信(其实是「形式上的信」)。概念的重复就更常见。在第七章中,我们会多谈希伯来诗体的对偶形式,不过在此可以先指出,散文中的对偶形式也像诗体一样常见,新约和旧约皆然。这是圣经中最常见的修辞方式。许多解经的基本错误,是强调一系列同义词中,各个名词的不同含义;例如,约翰福音二十章15-17节所用不同的「爱」字,希伯来书十章8节不同的祭,或腓立比书四章6节对祈祷的不同说法。我们总要警觉,使用不同用词或片语的原因,有可能只是文学的技巧,并没有神学的含义在内;重复或许是为了强调,我们不需要去强化各个名词之间的差异。
2.因果(cause-effect)和问题一解决(problem-solution)的关系,是先有某个动作,然后有某种结果。我们可以举无数的例子。先知对以色列的斥责,经常是采用因果方式。例如,阿摩司书二章6-16节开始为原因(「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」,6节),接下来则一一列举罪状(6下-13节),最后的结论为审判(或后果,14-16节)。阿摩司整卷书集中在社会的不公与以色列中猖獗的物质主义(如:四1斥责「巴珊的母牛……欺负贫寒的、压碎穷乏的」),以此为神审判的理由(四2,「日子快到,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上去」)。先知的弥赛亚应许,则可作为问题一解决的例子。问题是以色列公义的余民与背叛者一同受苦。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解决方法:他应许「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」(摩九8)。罪人将死亡(九10),但神自己却将「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」(11节,这意象取自住棚节)。
与此类似的是问题一回答的模式,保罗和先知都经常使用(参赛四十28-31)。在罗马书中尤其常见。保罗会提出一个修辞的问题(将他对手的看法表达出来),接着便回答这个错误的观点。这成为罗马书第三章的主要模式,开始是从犹太人的不信来看神的公平(三1-4),接着便从犹太人的不义来看神的公义(5-8节),然后谈到犹太人与外邦人都同样在罪之下(9-26节),由于需要信心,便无从夸口(27-28节),神不单是犹太人的神,也是外邦人的神(29-30节),信心能建立律法,而非废掉律法(31节)。在每个单位中,保罗都以修辞的问题开始,然后提出自己的答案。类似的问题也引介出因信称义(四l-2)、与基督联合胜过罪(六l-2)、律法与罪的问题(七 l-2、13)、神的拯救意图(八31-32),和神的公义(九 19一24,十一 l-2)等讨论。
在这个范畴内,我们也可以放入目的与结果或证明。这些都是在回答「为什么?」。目的将秩序倒转过来,说明原初的用意,而不单单只讲结果为何。这两者(目的与结果)常难以区分,不过诚如李斐德所说:「从神眷顾的角度来看,这两者的差异常并不重要」(1984:69)。无论我们翻译成「为了」(以未来为重点)或「因此」(以过去为重点),都是在强调神对全局的掌控。李斐德提到哥林多前书二章l-5节,保罗解释说,他讲道时不用高言大智,「叫(或译「因此」)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,只在乎神的大能」(亦参一29、31)。在这类例子中,目的与结果混合在一起。连接词「因为」常带进类似的神学观点证明。例如,罗马书八章29-31节说明,我们为什么可以知道「万事互相效力」(28节)。神已经预先知道他的子民,并且预定他们、呼召他们、使他们称义、得荣耀。换言之,神在掌控,所以我们能信靠他。 A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
B耳朵发沉
C眼睛昏迷
C恐怕眼睛看见
B耳朵听见
A心里明白
交错法在新约也很常见。隆德(Lund)认为,哥林多前书五章2-6节,九章 19-22节,十一章 8-12节等处,都有这现象(1942)。勃朗主张,约翰福音六章36-40节和十八章28节至十九章16节都用到交错法,他的论证颇具说服力(1966:276;1970:858-59)。
5.期待的转变(shifts in expectancy)包括许多种写作技巧。如尼达所说:「它们的重要性,就在于读者可以看出字的顺序、句法的结构,或一个字、词、句子的含义颇不寻常」(1983:36)。从某方面而言,这个范畴非常宽,可以包含修辞式问题、重复法或交错法。此外,它显然与象征用语重叠(我们将在本书第四章谈这方面)。不过,这类修辞方式超越了象征用语,是一种破格文体(anacoloutha,如尼达的说法)。然而,这类转变在结构的强调方面算是一项重点,所以必须包括在这里。耶稣的告别谈话(约十四-十六)中,有许多这类转变,因为数目太多,以致有些学者认为整段没有合一性,而是一系列重叠的传统,零乱地串在一起。结果他们提出约翰福音的「循环论」,或系列编辑说,主张这些人强将合一性加在第四卷福音书上,造成aporias,就是结构的不一致。不过,最近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发表,作者韦伯斯特(Edwin C.Webster)辩道:「这卷福音书,从文学的整体来看,结构十分严密,最基本的结构为对称的设计与平衡的单位」(1982:230)。韦伯斯特注意到,第十三至十六章中有两个同心圆式的段落,每一处都可分为三段(1982:243-45)。
有些学者将交换(interchange)列为另外一段,但事实上,这只是比较的另一种变化。交换不是直接的比较,而是轮流谈论人物、事件,或类别,以制造主题的比较。约翰将彼得否认主(十八15-18、25-27)与耶稣在亚那(19-23节)和彼拉多(28-40节)面前如一的勇气穿插写来,便是最佳的例子。彼得的胆小和耶稣的勇敢成为鲜明的对比。马可也用过类似的技巧,他把一幕放在另一幕之后,产生互相解释的效果。例子有:耶稣被自己的家人(三20-21、31-35)和文士弃绝(三22-30);医治睚鲁的女儿(五21-24、35-43)当中,插入了血漏妇人的事(五25-34),两者都与洁净的律法有关;咒诅无花果树(十一12-14、20-25)刻画出洁净圣殿(十一15-19)背后的意思,就是耶路撒冷的审判。在上文所提的亚当与基督之例中(罗五12-21),也有轮流的方式。
4.描述(description)是很广的范畴,就是用进一步的资料澄清一个题目、事件,或人物。这方法也可称为连续(参Osborne和Woodward 1979:70-71),它与重复不同,因为它将讨论「延伸」,而非「复述」。这种技巧之例,如约拿书一章4-17节为他逃跑(一3)的后续描写;或亚伯拉罕所蒙的祝福(创十三14-18)在十四章l-18节有更进一步的描述。另一个例子,是基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28-32节用了两个比喻,来澄清门徒「计算代价」的重要性(26-27、33节)。那里的信息为:若不清楚结局为何,没有人敢前来作门徒。这些比喻生动地描绘出,倘若一个人想要作门徒,却不「背起他的十字架」(27节),将会如何。基督要求人与世界完全断绝关系(33节)。
总结(summation)的原则也可放在这个范畴,因为它经常是在一长段的描述之后,将全文打一个结,说明最基本的主题或结果。当然,分辨出这种技巧,对判断一段经文的基本要点很有帮助。有时这类摘要出现在一段经文的头尾,例如约书亚记十二章7、24节: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所击败的诸王如下,……共计三十一个王」。多半时候,摘要出现在最后。在历史书中,这类摘要或「接缝」,有助于题材与主题的衔接。例如,使徒行传的摘要,含括了路加最主要的神学看法,就是在教会所面对的一切危难中,神的灵都能得胜。尽管有内部的分争(六 l-6与7节)、外在的逼 -/迫(八l-九30与31节)、暴君的迫害(十二1-23与24节),及异教的问题(十九 13-19与20节),但每一项摘要的中心,都是「道」的「增长」(这个术语一方面是指福音的宣扬,一方面是指其成功的结果,就是教会的增长)。
与摘要类似的,是犹太人重提(inclusio)的技巧,就是讨论到末了,作者又回来提他最初讲的观点。这个方法将一路发展过来的基本观念覆述一遍,成为整个叙述的总结。最好的例子之一为约翰福音一章18节,那里是约翰福音序言的结论,且是一章1节主题的重复,即耶稣是神的彰显,并一直与父同在。勃朗(Raymond E.Brown)也注意到约翰的重提法,如在迦拿的神迹中,二章11节和四章46、56节;在约但河外,则有一章28节和十章40节;还有逾越节的羊羔,在一章29节及十九章36节(1966:CXXXV)。
犹太作家强调主题的另一个技巧,是交错法(chiasm),就是在连续对偶的子句或段落中,将字或事件倒转过来写。当然,旧约中经常出现这方式;以赛亚书六章10节ABC:CBA的结构便是一例(NASB):
一、耶稣与门徒
二、门徒与世界
1.耶稣洗他们的脚;他的榜样,十三 1-20
1.葡萄树与枝子的隐喻; 他爱的榜样,十五 1-16
2.犹大的离开 十三 21-32
2.世界的憎恨 十五 17-27
3.耶稣离开的对话 十三33-十四31
3.耶稣离开的对话,十六1-33
韦伯斯特主张,第十四章与十六章的主要部分有交错的关系,可以用来解释其中重复的主题。现代读者很难看出这种转变,可是古代人却很容易察觉和了解。如果我们明白整个结构的发展,困难便消失了。换言之,这一段并没有笨拙的不协调或重复,而是仔细设计的讲论。
高潮(climax)与关键(cruciality)也属于这个范畴。前者出现在故事中,后者则在书信中,不过两者都有相同的功能,即将作者基本论点的中枢或转捩点显示出来。医治被鬼附的孩童(可九14-29),高潮并不是神迹本身,而是那位父亲的呼喊:「我信,但我信不足,求主帮助。」这是马可作门徒主题的中枢,也成为第18-19节门徒失败的矫正,以及第29节信心祷告之必要前提。李斐德(1984:63)举了一个极佳的高潮例子,就是马太福音四章1-10节和路加福音四章1-12节中,试探不同的顺序。马太的故事,结束的高潮为世界国度的试探,这样的强调与他以弥赛亚为王的主题相配。路加则以圣殿的殿顶试探为高潮,因他的中心是圣殿,特别强调基督教来自犹太教,这是他福音书的主题之-。这两个故事的高潮,都是了解神学重点的要诀。同样,罗马书第九至十一章乃是该书的转捩点。今天大部分学者相信,这不是附加的一段,而是保罗从最前面讲到犹太人与外邦人都在罪与审判之下(一 18-三20),一路预备而来的论证。
最后,我要在此把尼达对省略(omission)的探讨(1983:33-36)也加进来。倘若某位作者刻意删去读者所期待的某一点,就造成「期待的转变」,让人惊异,也有强调作用。通常这类经文会省略特殊的字(如林前十三 4-7中的kai,或来一 5、8、10前言中的kai)。但是,偶尔会出现一种情形:原来的读者能明白为何会省略掉关键的字句,可是现代诠释者却感到非常头痛;例如,「那拦阻他的」(帖后二6-7)或「六六六」(启十三18),在解释与指认上的省略。对这两者的解释理论有上百种之多,可能我们要等到主再来,才能明白其真正的意义。
赞助商链接
- 本作者更多文章
- 基督教释经学手册(6)2010-02-26
- 基督教释经学手册(5)2010-02-26
- 基督教释经学手册(4)2010-02-26
- 基督教释经学手册(3)2010-02-24
- 基督教释经学手册(2)2010-02-24
- 基督教释经学手册(1)2010-02-24
- 赞助商链接
- 热门文章
 耶稣医治十个大麻风病人(上)
耶稣医治十个大麻风病人(上)
作者:谢迦勒 2020-11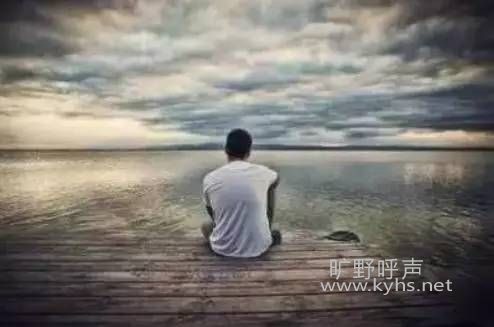 归回:得救在于归回安息,得救在于平静安稳!
归回:得救在于归回安息,得救在于平静安稳!
作者:温良大卫 2019-07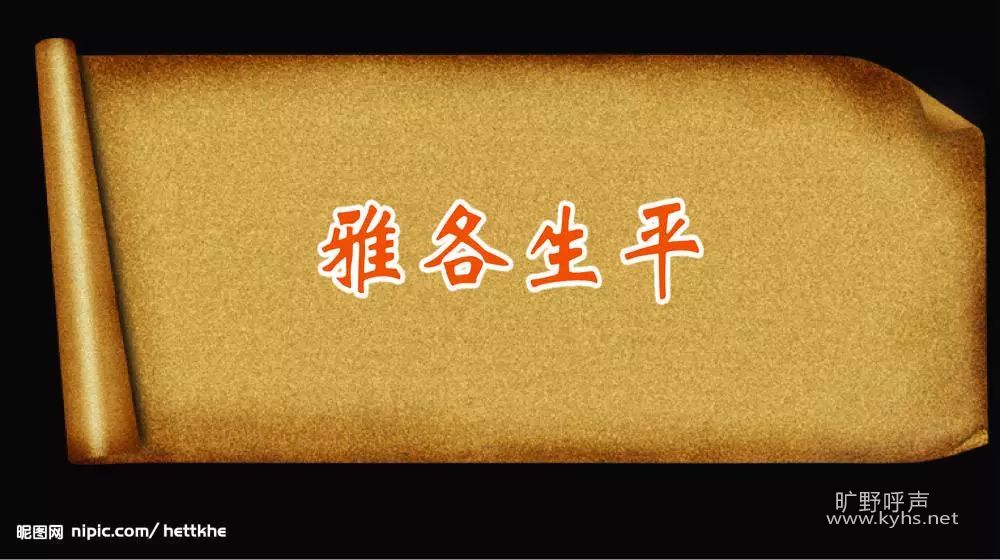 《雅各生平》第一讲
《雅各生平》第一讲
作者:蒲树忠 2018-04 看见复活主后生命的改变
看见复活主后生命的改变
作者:耶米玛 2018-01 主啊,求你可怜我!
主啊,求你可怜我!
作者:耶米玛 2015-01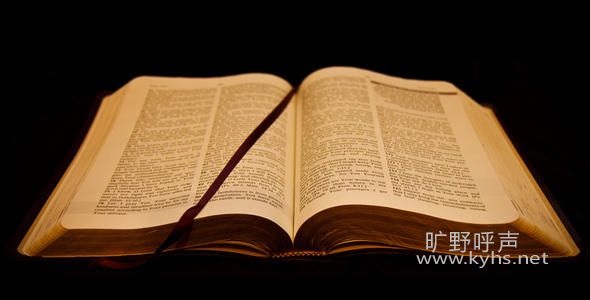 创世记38章查经札记
创世记38章查经札记
作者:陈亚群 2020-02 靠圣灵与情欲的争战的四个方面
靠圣灵与情欲的争战的四个方面
作者:阿斗 2017-0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