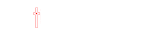母亲在她出生4个月时就去世了,然后,她被父亲送到奶奶家。6岁时,奶奶也去世了,父亲只好把她接回来一起生活。她回到所谓的自己的家,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妹妹、一个弟弟和一个比父亲小4岁的女人王香。她遵照父亲的指点,称王香为“妈”。但直到10岁,她才在书本上知道,按照家庭成员关系的准确表达,王香是她的“继母”。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个词,而这时,父亲也已经去世一年多了。
江一虹16岁时,继母王香再婚,将她也一起带到了新丈夫庄景家里。王香自己也是在继母家里长大的,有过一个刁钻古怪的继母,王香就发誓自己成了家,绝不虐待儿女,哪怕是别人的儿女。自己受过的苦,不能让别人再受。当时决定再嫁的时候,她就和庄景谈好了,自己的事自己管,两人就是搭伙过日子,她愿意做些让步,只要对方能帮着她把三个孩子拉扯到18岁,其他的事,庄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
惟独一件事后来起了争执,就是江一虹读书的问题。王香答应江一虹,让她读到高中毕业,那时,她已经在全年级排到前三名了,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和学生会副主席。每次开家长会,王香都感觉自己特有面子。但庄景不这么看。庄景认为女崽读不读书都行,读了也是白读,莫不如早点儿出去工作赚钱养家。这样的争执,差不多在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都会出现。江一虹从来只是听着,一言不发。直到有一天,庄景说着说着,开始激动,伸手摔了一只碗在墙上,江一虹放下手里的碗筷,淡淡地回了一句:“爸要是觉得我上学上得不应该,就和妈再生个孩子吧,我退学回家帮你们带孩子。”
她说这话的时候,眼睛一直看着庄景,直看到他扭过脸去,她才蹲到地上,把碎碗一片一片地捡起来。
江一虹说这话,是有内涵的,这内涵庄景自然是明白的,所以他胆怯,不敢再做声。王香也是明白的,却非常惊讶。她揣摩着,江一虹一定是知道点儿什么,不然不会这么准确地打到庄景的“穴位”上。
许多年之后,江一虹回想起当年这场无硝烟的战斗,都会忍不住笑起来。而那个秘密,她始终不曾告诉过任何人,后来王香多次试探过,想知道她是怎么知道庄景是同性恋的。但她听了继母的试探,却假装出一副懵懂的神情,将话题巧妙地移开。有些场景,她始终不愿去回忆,慢慢地,那些记忆都随着少年时光,被她一起抛弃在故乡的小镇上了。
离家去京城上大学的前一天晚上,她对王香说,我知道你当年是为了把我们养大才又嫁的人,等我毕业了,赚了钱,我就把你们接走。
她第一次看见王香在她面前流泪。
可惜这个心愿她没能实现。
二
江一虹的大学读得很幸运,成为中国最后一批不收学费的大学生。在学校读书的时候,她最热衷的不是学生会的各类选举——她始终觉得那种气冲斗牛的激昂姿态过于幼稚和造作——而是做小买卖。她虽然喜欢读书,却不是书呆子。她很早就培养出一种敏锐的能力,在街上走一圈,逛几个小店,她就能迅速地捕捉到市场的需要。那个时候,还没有网络,更没有淘宝,江一虹完全靠着细密的计算和对金钱的热情赚来她的第一桶金——500元人民币和20美元。当时,500元钱相当于一位大学讲师三个月的工资。而这却是江一虹在一个学期赚到的,那年,她22岁,上大学三年级。她从老家批发来各种风味干果和小点心,按类分包,插上统一的牌子,取名为“甘の味小吃”,听着仿佛出自遥远的日本,却在各宿舍的门口卖得异常火爆。临毕业前,她已经在各个大专院校做起批发生意来了。不过,她毕业后,做的几个职业,都与食品无关,倒是经常和电脑什么的有关。可算是直接地一脚就踏上了时代的最前沿。
毕业后,她先进入一家高校的电化中心做助教,其实就是做中心主任和副主任不愿做的各种杂活。
如果当初,江一虹愿意靠着一张脸蛋吃饭,她完全可能在那个二流都算不上的大学弄个处长做做,但她的自尊心太强,也太看重自己的智商。对照21世纪中国知识女青年的标准——宁肯坐在宝马车里哭,也不坐在自行车后笑,她似乎有点儿迂腐,或者换个更通俗的词儿,就是——有点儿想不开。
刚毕业没多久,继母王香带着江一虹同父异母的弟弟外出参加婚礼,出车祸去世,一车人走了五个,有两个和她有关。在整个后事处理的过程中,江一虹感觉自己似乎一直很恍惚。自始至终,她没号啕大哭,也没涕泗连连,一副平静到冷漠的面孔,让七姑八姨的看着非常不满意,私下里认为她出去读了几年书,人变得特别没感情。
按规矩,晚辈都要戴孝,大热天的,粗布做的孝帽捂得人一头汗,江一虹被七姑八姨劝了不下五回,才算勉强戴上孝帽。她倒不是怕出汗太闷,实在是觉得那个样子太诡异,让她难以接受。
更糟糕的还在后头。
按规矩,由长子或长女先跪在棺材前面大放悲声,然后烧黄纸,然后摔碎一只瓦盆,是谓“上路”,并连喊三声——“走好哎~~~”。才算是完成整个葬礼程序的第一回合。
这一次,任凭大家说破嘴,江一虹就是不肯跪地上烧纸、摔盆和大喊,她觉得这些规矩真是太愚昧了,她无论如何做不来。正在彼此争执不下的时候,妹妹一彩主动申请,替她承担了本应由长女承担的烧纸、摔盆、大喊的工作,总算把家人的面子圆了下来。
事后,左邻右舍七姑八姨都认为,江一虹的大学算白读了,连人情世故都不懂,估计日后找男人嫁出去的可能性怕是很小。
说起来,也算难为江一虹了,一场葬礼,往来的亲友关系极为复杂,有父系的有母系的有继母系的有继父系的,反正葬礼一结束,呼啦啦跑来吃饭喝酒划拳的就把当地一家酒楼的两层大厅都占满了。继父庄景事后一个劲儿地抱怨说,葬礼的花销太大了,收上来的那点儿人情费根本不够干啥的,房子又年年漏雨,而且刚上高一的妹妹一彩也马上要交学费了……一条一条摆明了是说给她听的。江一虹当时手边有几个钱,但她知道庄景不会没有钱,就轻描淡写地提了两句交通肇事方的赔款问题和遗产分配方案,庄景马上就不说话了。
临上火车前,她给一彩偷偷塞了200块钱,那差不多是她一个月的工资。
赞助商链接
- 本作者更多文章
- 给青年基督徒的职场建议2014-12-20
- 三个约瑟留下的榜样2014-10-07
- 信心的仰望成就应许2014-07-04
- 什么样的侍奉能讨神喜悦?2014-06-17
- 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10句经文2014-06-03
- 在井边2013-11-18
- 问题要从根源开始解决2013-07-15
- 经历熬炼,学会感恩2013-05-31
- 悔改的道2013-01-01
- 赞助商链接
- 相关文章
- 热门文章
 旷野呼声:上帝,我向您投降!
旷野呼声:上帝,我向您投降!
作者:勺勺.天爱 2019-06 主啊, 救我!
主啊, 救我!
作者:勺勺.天爱 2019-03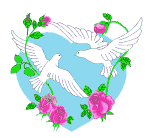 归宿(9)
归宿(9)
作者:沐雪冰蕊 2006-02 贝壳讲的故事——癞蛤蟆与天鹅
贝壳讲的故事——癞蛤蟆与天鹅
作者:恺盟夏 2016-06 微小说:回家
微小说:回家
作者:言雨 2015-09 基督里的爱情——我在这里等你!
基督里的爱情——我在这里等你!
作者:勺勺.天爱 2019-02 沙滩,记得我和你偷吃禁果的那一场哭泣!
沙滩,记得我和你偷吃禁果的那一场哭泣!
作者:勺勺.天爱 2019-07